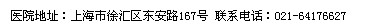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额窦炎 > 额窦炎常识 > 宋林峰野马与尘埃
宋林峰野马与尘埃
野马与尘埃
宋林峰
公元一九七四年,法国人罗兰·巴特终于踏上了这片东方的土地。从他略显凌乱的日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旅行社官员连续地、寸步不离地出现,才阻碍、禁止、审查和取消了出现惊喜、偶遇事件和俳句(诗意)的可能性。
第N则读书笔记宋白
1
我的妻子张伟突发奇想,要与我合写一篇小说,那一夜窗外电闪雷鸣,她的决定对我来说如同一个奇迹,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场灾难。我翻箱倒柜从书桌下面某一个狭长的抽屉里抽出一沓泛黄的稿纸,这摞纸堆在那里究竟存在了多久我也记不太清楚,上面都是一些残章断句,我尽量避免将自己的视线落在那些布满灰尘的字迹上面,我对她说:“找到一些感兴趣的,续写出来吧。”张伟接过我手中的残稿,眼神不经意流露出一丝坚毅。我无法判断。
下面来说说那个举止怪异的女孩。那个女孩很瘦,我估计她的体重不到一百斤,和她第一次在图书馆打照面的时候我着实吓了一跳(当时我以为自己撞到了她,而实际上却没有,我打了个趔趄,她却轻松地一扭身子躲避开来),她吃力地搬着十几本书,腰肢乱颤,走一步,向左略倾斜,又走几步,身体像一个弹簧似的又掰直了。我一直望着她的身影直到消失。那一天,本市还发生了一件大事,直到晚上,成千上万的市民在劳累一天过后,享受了精美的晚餐,当他们坐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换着电视频道时,才得知了这一新闻,而作为事发现场的目击者,我早已掌握了这起新闻的关键因素。当时图书馆正值下班时间,馆内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并无读者,我也是刚走出图书馆时才发现身穿制服的工作人员们一拥而出,身后的建筑物发出巨大的怒吼,像是地震又像是惊雷,一阵接一阵,下意识地,逃出来的人们都闪电般趴在地上,但是仅数秒过后,人们发现情况并不是自己所预估的那样,于是他们站起来,继续跑向四面八方。几个小时后,记者风尘仆仆地赶到了中心图书馆,只拍到了一些乱糟糟的黑乎乎的焚毁过后的纸张,有的灰烬随风起舞,场面十分凄凉。记者只好随机采访了一位消防员,那位消防员喘着气,坚定地说:“没有人员伤亡,一切尽在掌握。”这些画面通过电视信号再经过视觉器官得以转换,引起了许多市民的不良感受。据说,当晚一位中年妇女看到这条新闻后,导致了流产。当然,只是据说。新闻总是不缺这样的边角料,后来又有小道消息称,她之所以流产是因为担心自己的丈夫,也就是那位消防员。那位女孩的怪异举止并未能引起其他人的足够注意,我能发现,实属偶然。
一天早上,我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印堂乌青,我赶紧翻出老皇历果然右下角写着:出行安葬破土。但我后来迫不得已出门实属事出有因,那天的西北风不小,天干物燥。走在某条小巷中时,我亲眼目睹了一根杨树枝被风吹断,起先那根树枝在我头顶哔哔剥剥作响,我茫然四顾毫无头绪,等我走出了几步,那根树枝猛烈地撞击到地面上,叶子散落一地。也就是说,我侥幸逃过一劫,惊魂甫定,我以为这样一来,既然已经触了霉头,出行就不再是大忌了。更离奇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这条小巷的尽头人声鼎沸,但我一直朝前走,却始终走不出去。太不可思议了!小巷尽头的光亮就像一个瓶口,尽管我时而奔跑时而慢走,但都无法抵达。我在怀疑这是谁在跟我开的一个玩笑,我突然想到,为何不试着从来的方向进行突破呢?于是,我开始调转方向,朝来的方向原路返回。俗话说,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我暗自琢磨着,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何时走在了一条岔道上,这条小路两边芳草青青,万条垂柳。我立马闭上眼睛,等稍适应,才缓缓睁开。
此时,一个衣着古怪的老妪(无法确定,只是状似)向我姗姗走来,她的背佝偻成弓形,步履的节奏也毫无规律。她走近些,我发现她的头发稀疏到只剩下了几根荒草,一种莫名的荒芜的感觉顿时占据了我的心。我怜悯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她,她每前进一步(或者只能算作半步),我的心里都“咯噔”一下。大概在距离还有三米的时候,她轻咳一声,缓缓抬起脸来。她的头从后面抬起来——我才发现刚才她一直在倒退着行走,一袭黑衣使我无法分辨她的正面和背面。她微喘一声,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小丑之家。”她的声音像一团黑色的烟雾弥漫在我的周围,我的思绪被阻塞在某个地方,无法抽离。这时候一缕阳光斜斜地泻下来,她的衣服逐渐变白、变黄、变红……
后来我似乎是昏倒了,所以请原谅我无法回忆起全部的细节。我的喉管仿佛被谁卡住了,我喘不来气,我醒来的时候眼前是温柔的妻的娇美面庞。
“怎么了?一身的汗。”
“没……没什么。有点热罢了。”
张伟端给我一杯牛奶,另交给我一张A4纸,上面有几段文字,显然是某段小说的开头:
“奈落是我的名字。我出生的时候我母亲就站在门口,那一日晨光熹微,她冷笑的样子让我爹怀恨在心。当我的脐带被产婆娴熟地剪断之后,我终于成为一个人了。我爹眉开眼笑,重赏了那个嘴角带黑痣的产婆。产婆的嘴张到很大,她不停地恭维道:‘恭喜!恭喜!’一向愁眉苦脸的管家老贾于那天也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
‘老贾,把我的马牵来。’
‘是,老爷。’
‘你还愣着干什么?去准备吧。’我爹冷漠地对母亲说。母亲没有说话,她转身离开了,她脚步轻盈,像极了一只檐下的燕子。”
2
张伟擦桌子的时候分外用力,桌子上长时间以来滞留的污垢都被她精准地祛除了。她的十个指头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被消磨得格外迟钝,前不久她切菜时一时疏忽,刀就那样出乎意料地削掉了她的一小块肉,但她竟然一声不吭。她来卧室取创可贴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些分布不均的散乱的血点子沾在她的浅白围裙上。对于危机的应急处理,她表现出了超常的冷静。这一切都是从她开始有了写小说的想法时开始的。
说实话,我想劝劝她,但不知如何开口。
在一个周三晚上,在纷乱的电视频道中,我注意到一条电视新闻,记者说市图书馆发生了火灾。张伟也坐在沙发上,我们面面相觑,那个地方我们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俩都不愿相信这条新闻是真的。张伟的惊讶程度显然是超过我的,这从她急忙拿出手机拨打新闻热线的举动可以看出。她的手不住地颤抖,因而她和电话那头的人在谈的时候声音也极不自然。过了一会,张伟黯然地放下了电话。怎么了,我问。没事,她说。她走到厨房里,我听到水滋滋的声音,她在洗脸,或者只是单纯地洗手,我只听到水声。张伟的神经质还表现在需要我俩全情投入的房事上,在我奋力匍匐的时候,她的瞳孔会突然放大,有时候我甚至以为她的眼珠就要迸出来了,心中掠过一丝恐惧,我们的事也就无法再继续下去了。事后她说,她在寻找一种感觉,以前没注意过的,当下需要捋清的一些感觉。我对此表示了怀疑。我不认为在肉体上除了皮肤的接触和摩擦,除了那个时刻喷发的快感以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感觉。张伟说,你迟钝了。她的话毫无逻辑和根据,因为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她皮肤的光滑与柔软。
每晚,她会抽几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电脑前敲击键盘,然后把文稿打印出来,在很多时候,她会央求我听她读一小段,今天晚上她读道:
“我一直坐在山上,炽热的阳光从后背爬到了我的脸颊,起初我以为是一只蚂蚁或者其他的小东西跑到我身上了,我伸出手去摸,什么也没有摸到,我才知道,太阳已然变得昏黄。脚下的这条小溪曲曲折折不知道流向什么地方,我总想着有一天可以顺流而下去看看它的尽头。
“奈落。——有人叫我。
“新月向我跑来,她像跑在细雨微风中,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她那天裙子上的褶皱纹路,确切点说,是汗,一些微小的汗滴在她奔跑的时候制造出了细雨的效果。那个黄昏,新月的出现简直美如一幅画。至今,每次回想,我心里都充满了感动。”
图书馆的失火给我带了极大的不便,这段时间以来,我无处可去。我更怕待在家里,张伟敲击键盘的声音像木鱼单调的声响,令我无比烦躁。写作的灵感也离我而去,我的生活正在走向绝望、无助和毁灭,一日三餐成为机械的进食,睡眠演变成无休止的失眠。后来某一个夜里,我突然顿悟了,目前的糟糕状态全是因为我的生活失去了依靠(写作),我的这一精神支柱正在被张伟盗窃。我撑着惺忪的睡眼,张伟并不在我旁边,她没睡——嘀嗒嘀嗒,隔壁屋子里传来隐约的键盘声。我复又躺下,用枕头使劲儿地按住脑袋,那声音却阴魂不散,我浑身哆嗦,像一个疯子般在床上滚来滚去。凌晨张伟打着哈欠走到床边的时候,她的尖叫把我从朦胧中惊醒。
“你怎么了?”她惊讶地问。
“我不知道……我……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我有气无力地回应道。
张伟若有所思地皱起眉头,嗫嚅着说:“宋白,其实,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谈谈……”
“不,什么也不用说了,你用心写你的小说,我三天后回来。”我们很快达成了协议。早饭过后,张伟把我换洗的衣物整理到拉杆箱里,送我到楼下。我坐在出租车里,透过车窗,依稀看到她泪眼婆娑。对不起,我需要冷静。我于子夜时分到达宋寨。夜空疏朗,凉风习习,街道里偶尔传出几声空空荡荡的犬吠。在望云山的山脚下,有一处(带院子的)房子是我们之前度假时候租用的,租期三年,今年算是提前用上了。钥匙捅进锁里,发出锈蚀的摩擦音,我拉着箱子,走进院子。站在院子里抬头看,是城市里没有的东西:星空。
第二天,左邻右舍知道我回来了,都拎着东西来看我。有的带了一只鸡,那鸡看上去十分凶猛,大概是散养的,野惯了,有的挎着一篮菜蔬,他们都热情地走进屋子。有一位老乡还牵着孙子,那孩子看上去十一二岁,老乡说:“该上初中了,这娃愣是不想上,”他嘬一口烟,鼻翼翕动了几下,“其实俺明白,孩子爹妈都不在家,他是想找个挣钱的营生。”说罢,深情地抚摸了孩子的头。那小孩胆怯地望着我,那眼神令我感到虚空。人流散去之后,我决定上望云山一遭。望云山并不高,山坡上栽满了榆树,还有这里最常见的一种槐树。我循着一条羊肠小道,徐徐前行。上山的路两旁布满了一些坑,大部分不见底,这些坑是早年人们私挖汞矿留下的,现在成了望云山的伤疤。望云山实在是一座小山,这里距我们常度假去的通天峡还有几公里。没多久,我就到达了山顶,山顶布满了大小不等的碎石,踩上去,凹凸不平的地貌像在脚底按摩。
一丝凉风吹过来,我极目远眺,葱葱郁郁的树微微摇晃,构建出一个世外桃源。我想在此小憩片刻,遂找了一块大青石,轻靠着,闭上了眼睛。在这片刻宁静之中,我心中的懊悔(以及对张伟的愧疚)猛地翻涌而来,我是一个冷血的人吗?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的伴侣呢?我没有勇气再往深处想,一切决定都似乎出于偶然,可一个简单的偶然却造成了我们之间感情不和的假象。我发誓,我是深爱张伟的,我们结婚至今,从未变过。
奈落,奈落。你在这儿干什么?
谁是奈落?谁在叫奈落?
我急忙睁开眼,环顾四周,并没有什么人。野草茫茫,顺风倾倒。间隔了大概几秒钟,一群孩子(仅仅是凭借体型的第一判断)出现了,他们排成一条直线,嘻嘻哈哈地向我走来。打头的个子较低,却戴着一个大花脸,跟在他后面的每个人都戴着不同的面具,加上他们走路的姿势,平添几分戏谑。碎石在他们脚下发出碰撞的响声,空气的流动出现曲线。他们在离我大概三米远的地方停下来,像是收到了其中某一个的指令,又像是完全自发的不约而同。很快他们就围成了一个圈,每个人之间空了一臂的距离。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其中的一个就迅速地蹲下捡起一小块石子砸向对面的某一个,“通”的一声闷响传入我的耳朵。被砸中的那一个也蹲下去重复了之前那人的动作,他又砸向了另一个人……他们在干什么?我就在一旁看着,他们不停地蹲下又站起,一轮接一轮地发起攻击。我当时以为他们一定是疯了,但后来我却不这样认为了。我觉得自己仿若处于一个平行世界,只能接受这一切的安排。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了,无法开口说话,无法向前踏出一步。唯一存在的,是我的思维。从遥远天际逐渐逼近的雨丝终将我编织到这张大网之中,冰冷的雨滴落在我的脸颊,但他们的游戏仍未结束。
3
“少爷,你看那个秋千。看见了吗?”
“看到了。”
“还记得老爷吩咐过什么吗?”
“记得。”
“我们走吧,回家。”
“老贾,我不喜欢别人问我很多问题。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
“是的,少爷。”
三更天,我去敲了老贾的窗子。我希望他给我一匹马,以便我能在那辽阔的平原驰骋起来,追逐我心爱的姑娘。新月已举家搬迁,我必须日夜兼程,才能追赶得到她。
“少爷,你不能这样做。”
“我必须去。”
“不,我要先去禀报老爷。”
“别废话。”
老贾已经是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我只稍微用力,他就轻飘飘地倒了下去。我如愿以偿地拿到了马厩的钥匙。那匹枣红色的小马驹不停地喷着响鼻,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活动活动蹄子了。
“马儿啊,马儿,我们出发吧!”
凌晨张伟打着哈欠走到床边的时候,她的尖叫把我从朦胧中惊醒。我跌倒在地上。
“你怎么了?”她关切地问。
“没……没什么,只是做了一个梦。”
“梦?什么梦?”张伟追问道。任我搜肠刮肚也无法忆起梦的一星半点,我只好说:“不记得了。”
“哦。”随后张伟给了我几张纸,她躺到床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我现在无心看她的小说,我要出门一趟,因为刚才上洗手间的几分钟里,我收到一条短信:小丑之家见。小丑之家?这个名字就像一条鱼似的在我脑海里扑腾几下,又瞬即平静下来。请原谅我的梦境总是冷不丁地掺和到现实中,我仔细回想,好不容易才捋清楚了这个名字的来龙去脉以及和我之间的关系。这还是前几个月的事,张伟的表弟我的朋友张雨生有一阵子常来我家,和张伟商讨搞一家独立书店的事,开书店,我是百分之一万的支持,至于资金,只要符合条件,贷款我也支持。既然我没什么意见,张伟和雨生讨论的就是细节问题了,这些细节问题我很少过问,我不是琐碎的人。有一天,张伟打电话给我说,书店名字就叫“小丑之家”,我当时没在意,因为最后张雨生从我们这里得到的支持也就是借了几万块钱,后期全部是他自己一手倒腾策划。现在我想起来了,这条短信约我去的就是这家书店,这家已经开张的书店。
洗漱完毕,照镜子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印堂乌青,我赶紧翻出老皇历果然右下角写着:出行安葬破土,但我必须赴约。那天的西北风不小,天干物燥。走在某条小巷中时,我亲眼目睹了一根杨树枝被风吹断,起先那根树枝在我头顶哔哔剥剥作响,我茫然四顾毫无头绪,等我走出了几步,那根树枝猛烈地撞击到地面上,叶子散落一地。也就是说,我侥幸逃过一劫。等等,这些情景怎么似曾相似?最近持续的失眠使我的精神状况极其糟糕,我敢肯定,在我的某一个梦中,这些场景出现过。出了小巷,向右转,就看到了“小丑之家”,我深吸一口气,昂首阔步地朝那里走了过去。书店的布置古朴典雅,精致的灯具散发出浪漫的光线,一本本书籍安静地躺着它们的位置上,情调尽显。现在的书店装潢真是情怀满满,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平心静气地来到这里坐下翻开一本书然后陶醉其中,记得之前张伟还没有写作的念头时,曾打趣道:“现在除了你们这些作家,其他人很少读书了。”张伟说得不无道理,我既无法反驳,又觉得不舒服。但我无法改变,谁也无法改变。这大概就是时代。什么是时代呢?我想,时代大概是无法定义的。我到一处沙发坐下。此时,手机来了一条短信:欢迎来到小丑之家。到底是谁?能够这么精准地知道我到达这里的时间?我站起来,环顾四周,并没有熟悉的身影,鬼祟的可疑人物也没有发现。我有点沮丧。我向收银台询问有没有包间之类的地方,他们摇头表示没有。我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我随手在某个书架取了一本书(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在沙发上百无聊赖地看起来。当我云里雾里地把这本书读完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小时之后,我打开手机,并无进一步的消息提示,这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打电话给张伟,无人接听,她可能还在梦里。我又向前台要了张雨生的电话(他的电话号经常变动),同样无人接听。真是咄咄怪事。
我决定到市图书馆那里看看。到了以后才发现,周围早已拉起了警戒,重建工作还未展开。在街对面的市美术馆门口,我又一次见到了那个女孩。她在那里支起了一个摊位,上面堆满了一些旧书。果然不出我所料,纵火犯就是她!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准备报警,但是一种恶作剧的心理又促使我转变了想法。事后回想,我到底是被她迷了心窍还是别有其他原因呢?这个问题没有困扰我很久,就忘却了,因为嫌犯被抓的那天作为都市报的记者张伟就在现场,她还不忘在第一时间抓拍了一张照片传给我。我走到摊位前,大致浏览了一下那些书籍,几乎每本都是绝版的,拿我熟悉的文学类来说,特别显眼的是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译林出版的老版《卡尔维诺文集》,这几本书目前在市面上很难买到,倒是在一些二手书网站有人高价兜售。我又仔细观察,发现这些书不同程度地被做了手脚,尤其是在书的第一页和书的边缘处,有用小刀抠过的痕迹,而很多书的第一页是缺失的。这不难理解,她用这种拙劣的手段去掉了市图书馆的章印,以此来掩饰这些书的来路。一个奇怪的想法浮上心头,我不能让她再错下了,我深情地注视着她,语重心长地说:“姑娘,回头是岸啊!”她呼啦一下站起来,疑惑地看着我,又翻翻摊子上的书,说:“没有《回头是岸》!”我厉声道:“别再干这些事了!”突然提高的声调把我自己也吓了一跳,那姑娘更是怒目圆睁,“神经病!”她说。
我悻悻然回到家的时候,张伟已经在厨房准备晚饭了。我想和她说一下小丑之家的事,但想了想还是算了,如果张伟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呢?我可不想在她面前丢脸。吃饭的时候,张伟异常高兴,可以称得上是眉开眼笑了。“今天又完成了一章,宋白,我现在才发觉,自己其实是有这方面的天赋的,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哈,你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谁是玉,你?”
张伟使劲点点头。我伸手摸了一下她的额头,“没发烧呀!”
“讨厌!”
临睡前,张伟又交给我一张A4纸,她小说的最新进展。
4
“你听见了吗?是他来了。”
“小姐,你说的是奈落少爷?”
“奈落……奈落……”
“小姐,你看那月亮升起来了,夜晚来了啊,小姐。”
“我听到他在喊我的名字。”
“不会的,小姐。我们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在逐渐腐烂,我们与这泥土正在合二为一,就连我们俩的骨头,现在也已经分不清谁是谁的了。”
“这么说,我和他不会再相见了?”
“小姐,尽管这很残忍,但我希望你明白,在他的这一世是不可能的了。”
“……”
“小姐,小姐!哦,你是对的,睡吧,你还是睡过去的好,免得伤心。”
我隐约听到了哭泣声,这是一种轻柔、尖细的哭声。我慢腾腾地从床上起来,看到了张伟的脸上正梨花带雨。“怎么哭起来了?”
“故事结束了。”
“你在说什么?”我以为自己听错了。
“我的小说完成了。”似乎是一种无法言说的悲痛使她的身子看上去都弱不禁风了,我过去拥抱了她,她的脸落在我的肩头,近日的所有不耐烦都烟消云散了。张伟,仍旧是我深爱的张伟。良久,她歉疚地说:“这段日子,实在抱歉。”不期然,她说出了这样的话。我抱紧了她,我听到了她的泪扑簌簌地掉落。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粗略计算也读过有上千本小说,这些小说构建着各式各样的故事,有的令我感动落泪,有的让我忍俊不禁。但是当我得知自己无意之间进入张伟的圈套时,我竟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事情是这样的:
“小丑之家”的预计开张时间是两周前,好吧,准确点,九月十五。张伟和张雨生提前商量好要给我一个惊喜,我只能说事情本来是这样的。但是由于一些手续没有到位,“小丑之家”的开张便推迟了一个月。张伟当时用某个APP设置了一条定时短信,哦,不,是两条。第一条便是“小丑之家见”,第二条是“欢迎来到小丑之家”。但是后来开张推迟她忘了取消短信设置,于是,九月十五那天我还是准时收到了这两条短信。而后,我莫名其妙地到“小丑之家”又枯坐几个小时,全拜张伟所赐。这是我和张伟谈心的收获。近一个月来,我们都没有这样坦诚地交谈过。我告诉她,在轻度失眠的这些天,我做了很多梦,这些梦我并不全部记得。但是其中两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张伟,我梦见我回到了咱们在乡下的那座房子,在房子背后的那座小山上,我见识了一群孩子,他们在玩一个游戏;还有,有一天晚上我还梦到我走在一条小巷中遇见了一个奇怪的老妪……张伟对我这些奇奇怪怪的梦嗤之以鼻。我当然也明白老妪口里的“小丑之家”只是现实中“小丑之家”书店这一名字的模糊投射,再加上毫无逻辑的勾连,创造出来的效果。至于那些孩子们玩的游戏,难道和他们脸上戴着的面具有什么关系?小丑面具,对,应该也是潜伏在我脑海的“小丑之家”这个名字(如前文所述,我第一次得知这个名字是在张伟的电话中,后来我逐渐淡忘书店的事情,直至收到张伟“小丑之家见”这条短信才又想起这一名字)在作祟,这是我运用弗洛伊德理论分析得到的结果。
当天晚上张伟还为我带来了一条消息,市图书馆的纵火犯已经被捕,她当时就在现场。当然,早些时候她已经给我传来了图片,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忧心忡忡起来。
张伟说:“嫌犯是个小姑娘,那么年轻,可惜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默默地跟着警察上了车。”
我问她:“具体在哪里抓到的?”
张伟想了想,说:“就在市图书馆对面,她也真够胆大的,还敢在那里出现,警察就来了个瓮中捉鳖,额,不对,是守株待兔。”
我对她不合时宜的成语运用丝毫无感。
“还有哦,听周围的人说,这个女孩精神有点问题。”
我陷入了沉思。是她吗?真的是她吗?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动机是什么?应该不是精神有问题这么简单。作为一个小说家,这起事件的背后像是有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吸引着我。我务必要探明真相。翌日,我独自来到了市美术馆。果然,那个小书摊不见了,不知道那女孩现在受着什么待遇,有没有遭到粗暴对待?转念一想,应该不会,现在提倡文明执法,她如果坦白交代,应该不会受什么皮肉之苦。美术馆正在举办一场展览,是本地的一位著名画家的作品,我踅进去,想看看这位朋友(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最新佳作。遛了一圈,感觉没啥新意,就出来了。正当我将要离去的时候,那个小摊位出现了。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到她的跟前,上下仔细打量着,十分惊讶:“这么快就出来了?”姑娘眉头紧皱,并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又问她:“这么快就出来了?”这次,她像是被激怒了,抄起一本书就朝我砸来,我慌忙躲开。“别……别着急,你听我解释。昨天,那个,警察,图书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试图表明我并无恶意。但是我一激动,句子就变成了词语,孤零零地无法联结左右产生意义。情急之下,我掏出一张名片扔给她,又隔空喊话:“明天下午五点,美术馆里见。”我指指背后的美术馆。
第二天,我并没有再见到她。大概是一周之后,我收到一封邮件,看来信地址,像是临时申请的邮箱。
宋先生,你好。
感谢您的关心。我想您是认错人了,图书馆那件事情我知道,说实话,我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但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
我姐姐和我是双胞胎,直到现在,我们长得也是如此相似,您大概就是因此才错认的吧。去年,在图书馆的招考中,我姐拔得头筹,无奈在面试时被刷了下来。起初,她以为自己实力不济,郁闷了几天之后就着手准备其他的考试。我爸妈去世之后,一家的经济来源全部靠她打工所得。招考结果公布后,我姐才知道,她是被人“挤”下去的。她不服气,但是投诉无门,她那么要强的一个人,那个疯狂的想法大概在那时就在她的心里扎根了。警察带走我姐那天,人们说她得的是间歇性精神病,一受刺激,会随时发作。真是荒唐至极。
我姐是无辜的,希望您能原谅她,莫追究了。
6
我的妻子张伟,前几个月的某天突发奇想,要与我合写一篇小说,那一夜窗外电闪雷鸣,她的决定对我来说像一个世界奇迹,当然,也有可能是一场天灾。总之,现在是盖棺定论的时候了。
我终于一口气读完了她的小说。“怎么样?”她迫不及待地等着我的意见,“你那天从抽屉里给了我那么多稿纸,我实在不知如何下手。后来索性从里面随手抽出一张,但很可惜,这张上面只有一句话,像是一句摘抄,上面写着:那时世间有个硕大的月亮。我看着你,看坏了眼睛。我就硬着头皮续写了一篇。”
“奈落最后怎样了?”我问她。
“你对这个感兴趣?”她反问。
宋林峰,青年作者。
熊森林陈志炜
洪家男
王辉城
朱聿欣
陈冬冬
锦年
颖川
陆支羽
予望
金周
兰童
炎石
陈文君
林侧
顾星环
風卜
王彦钧
李扬
焦窈瑶
朱慧劼
杨万光
索耳
林为攀
徐小雅
照人
陆俊文
郑然
溥小山
栗鹿
徐畅
砂丁
沈正攀
余幼幼
莱明
赵燕磊
高燃
三三
甜河
严天
周苏婕
叶飚
大头马
钟皓楠
小托夫
崔罗石
郑纪鹏
林羽竹
石梓元
刘家玮
岑灿
张凯
输入名字,获得作品
宋林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