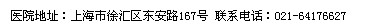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额窦炎 > 额窦炎常识 > 马家窑彩陶上的信仰
马家窑彩陶上的信仰
年第二届丝绸之路彩陶与嘉峪关历史文化研讨会
马家窑彩陶上的信仰
田波
本文,以拙著《春节考源》首创的社皇教之说,阐释羌文化。“鬼罐”之说,源于古羌葬俗,即马家窑彩陶之类的古董多见于墓葬。墓葬是宗教行为,信奉人有灵魂,而古羌认为女娲抟土造人的地点是在昆仑山;因此,有“入土为安”、“魂归昆仑”之说。女娲伏羲,甘肃民间奉为“人祖”,象征着华人的起源,是认同最广的中华共祖。这种信仰,称作社皇教,即中华民族宗教,主神是女娲,教主是伏羲。这种宗教,在炎黄时代,早已盛行;因此,甘肃神话对女娲伏羲当有传唱,与之时空接近的马家窑彩陶,亦有体现,比如:拉手而跳的萨朗、山水尽头的彼岸世界、与巫字相伴的蛙图腾、象征女娲伏羲交尾的卍字,等等。地球村时代,对民族宗教的这种追溯很有意义。
古羌、彩陶、信仰、人祖、卍字
(马家窑彩陶,人类学、民族学专家吴金光年摄于甘肃临夏博物馆)
引言
文明古国,唯有中华健在,而中华民俗以丧葬习俗最稳定,一旦被伟人创制出来,常人难以撼动,而相应的遗迹、遗物(包括马家窑彩陶)、神话、传说,未必臆造。女娲、伏羲,被华人奉为共祖,被甘肃百姓称作“人祖”,正是跟葬俗有关的伟人。
拙著《春节考源》首创的社皇教之说,认为:祖先崇拜是与人类同时诞生的宗教形态,族源神话里的主人公往往是民族宗教的主神。人祖是族源记忆里最早的一对夫妻,人祖崇拜的定型标志着民族宗教的定型。宗教不同,人祖各异,从而形成不同的民族意识;因此,人祖崇拜具有身份认同的作用。这一点,在马家窑彩陶上有所体现,比如:
①“鬼罐”之名,触及了中华民族宗教的核心——祖先崇拜。②彩陶上的山水纹,象征的是鬼魂通往冥界的漫漫长路,要跋山涉水,才能抵达,才能生死轮回。③彩陶上的蛙纹甚多,而以四周写着“巫”字的蛙纹最神奇,那是在表达女娲的重要身份-——高禖。④彩陶上多次出现的“卍”字,当是对“男女性交-伏羲女娲交尾”的写照;即言,“卍”字起源于易学的阴阳论。……
所以,需要回答:①马家窑彩陶是古羌遗物,传说女娲造人就在这附近,女娲伏羲的出生地离这里也不远;因此,古羌对女娲伏羲的崇拜彩陶有无反映?②马家窑文化,与炎帝、黄帝、蚩尤,在时空上接近,正是中华原始宗教的繁盛期;对此,繁盛了两、三千年的马家窑彩陶可有反映?③在族源上,炎帝、黄帝、蚩尤是“女娲-伏羲-神农”一脉的;因此,汉族、苗族等古羌后裔,都崇拜女娲。这些民族远祖,往往组成民族宗教的神谱;那么,这个民族宗教,叫什么?
马家窑彩陶的观赏性极强,审美研究已汗牛充栋,但并非基础研究,免做赘述,而它的一大基础研究,便是探索它体现了怎样的古羌信仰。在民族意识越来越淡的地球村时代,这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有助于重建我们的宗教学说、巩固我们的文化自信。
一、古羌冥器,鬼罐之谜
(1)鬼罐
千百年来,黄土高原上流传着“鬼罐”的说法。从前,人们往往在野外发现一些跟白骨埋在一起的陶罐,被视为不祥之物,称作“鬼罐”,倘若见到,往往砸碎。[1]考古证实,这种“鬼罐”,其实就是由于各种原因而暴露在野外的马家窑彩陶之类的冥器。俗信,骨头是魂魄的居所。因此,它可以视作“葬魂罐”,但不是“火葬罐”、“骨灰罐”。
“经过长时间研究,我发现马家窑文化彩陶,至今我们看到的所有器物,几乎绝大多数来源于墓葬。它都是当时古羌人的陪葬实物。”[2]“马家窑谱系的唯彩是葬,到齐家人那里转换成了唯玉是葬。”[3]这里的“彩”,指彩陶。“当地传说,女娲造人就在这附近。”[4]“年,考古工作者正是在传说是女娲的诞生地附近的村子里,收集到了这件六千多年前的立体人头型彩陶瓶,她镂空的双眼,目光深邃,整齐的头发,匀称的五官,使我们仿佛看到了远古祖先的形象。”[5]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马家窑遗址而得名,距今年至年之间。”[6]通过文献、考古、神话、遗迹等多重材料的研究,证实马家窑文化与炎帝、黄帝、蚩尤,在时空上接近;因此,很难说马家窑文化跟炎黄蚩毫无关系。再讲更古的,华人对女娲、伏羲的崇拜,定型于甘肃,传说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是女娲、伏羲的出生地,故称“羲里娲乡”、“两皇故里”。两皇,即娲皇、羲皇,即女娲、伏羲。因此,也很难说马家窑文化跟女娲伏羲毫无关系。
华人对女娲的崇拜,早于对伏羲的崇拜。《风俗通义》说“女娲抟黄土造人”,把造人的神说作是人类的母亲,其性质接近原始,因为这时是女娲单独造人,说明产生这个神话的时代,还不懂婚配生人之理。只有男女婚配才能生人的观念,要比处女感孕、捏泥造人之类的神话晚出得多。抵制兄妹婚的观念,则更晚。所以,伏羲神话当是父权制兴起后,逐渐粘附到女娲神话上的。
在神话史上,女娲是比盘古问世更早的开辟神、创世神。女娲神话产生于母系社会,“女娲”之名最早记载于战国屈原的《天问》;盘古神话产生于父系社会,盘古壁画最早出现于东汉的益州讲堂石室,盘古神话最早见载于三国的《三五历纪》、《五运历年记》。人类社会,母系制在先,父权制在后。男神开始受到注意而被歌颂,是父权制兴起乃至确立以后才有的事。中华民族具有完整即未曾间断的社会发展史;在中华神话里,最早的开辟神,当是一位女性才对。以女娲为开辟神,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痕迹。后来,将女娲说成是盘古,那是神话流变的结果,因而至迟在三国时代,才有盘古神话的记载。汉朝盛行的“三皇五帝”说,多把女娲列入三皇,但从未言及盘古,何况女娲的功德远非盘古所能比,让女娲位列三皇可谓委屈。所以,追述中华起源,当说“自从女娲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
女娲崇拜及其“女娲创世”说,是母系社会的产物,迄今已有数万年。从史影看,女娲或许是远古的女酋长,后来演变为神名、酋长称号、族称、姓氏。基督教及其“上帝创世”说,都是男权社会、圣父崇拜、男尊女卑的产物,迄今仅有两千年。
因此,在古代中华,从根本上影响华人的信仰,不是舶来品,而是本土的女娲崇拜。它承载着华人的族源记忆,是积淀最深的传统文化,甚至纳入国家祀典(即礼制),称作“社祭”。它的古老性、稳定性、崇高性、礼制性、完整性、鲜活性、海量异文、多民族性,等等,说明它是中华的本土宗教。
年,“苗妇有子,祀圣母;圣母者,女娲氏也。”(《苗俗记》)按俗,这是将自己以及自己的孩子都看作是女娲所赐,因此要祭祀谢恩。苗族神话《落天女的子孙》,讲:“很古老的时候,天与地创生了一位女神,称为‘落天女’。她来到凡间,因为吞吃了老人送给她的红果子,生下7个儿子,他们被玉皇大帝任命为雷公,专门监督人类要行善敬孝,否则将受到惩罚。最小的两个儿子戈生与戈瑟脾气都很暴躁,戈瑟用计将戈生囚禁起来。戈瑟的子女伏羲兄妹受骗,给了戈生水与火,结果用雷电炸开锁链逃走,并降下洪水报复。后来,伏羲兄妹结合,繁衍了苗族子孙,成为苗族先祖。”[7]
蚩尤,是苗族之祖,是历史上最显赫的苗王。“蚩尤,姜姓,炎帝之裔。”(《河图括地象》)“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遁甲开山图》)“蚩尤者,炎帝之后。”(《玉函山房辑佚书》)“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路史》)“蚩尤为姜姓,实系苗族。”(《岭表纪蛮》)汉族的古籍或传说,或云蚩尤号炎帝,或云蚩尤为炎帝九世。汉族,自称“炎黄子孙”;炎黄,即炎帝、黄帝。因此,苗族是汉族的近亲。
“伏羲生少典,少典生神农及黄帝。”(《轩辕黄帝传》)少典,即少典氏,是个氏族的名称。即言,黄帝是少典氏这个氏族的后裔。按照中华神话的神代世序,先有神农,后有炎帝,神农即神农氏(传说,不止一世),生活在炎帝一世之前,而炎帝七世姜榆罔,才与黄帝是兄弟关系。有了这些背景,才会有把蚩尤称作“炎帝九世”之说。显然,《史记》为了塑造黄帝谱系,将这些关系简单化了,混淆了神农、炎帝的关系。传说炎黄之世距今年,不论是与黄帝同时的炎帝八世姜榆罔,还是整个炎帝世系所对应的多年,都与距今年至年之间的马家窑文化有所对应。
整个炎帝世系所对应的多年:①炎帝“纳奔水氏女曰听谈,生帝临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厘,次帝里,次帝榆罔。自炎帝至榆罔,凡八世”。(《册府元龟》)②“神农皇帝归了天,长子归魁坐江山,一共坐了八十春,江山一旦付帝承,帝承接位六十年,帝明四十九年零,帝宜五十九年崩,帝莱江山六十八,帝里四十三年正,后生节茎掌乾坤,节茎生帝克戏,克戏才生榆罔君。江山共有五百二十春,乾坤一旦付公孙。”(《黑暗传》)③“炎帝神农氏第一代、第二代均在宝鸡。后逐步东徙到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第一代神农炎帝临魁。第八代神农炎帝榆罔,他老人家的陵墓在湖南炎陵县。”[8]④“炎帝传承八代,共计五百二十余年。各地祭炎帝,究竟是祭炎帝神农氏始祖还是第几代孙,不得而知。”[9]
历史学家,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故后世名其处曰鼎湖(胡),名其弓曰乌号。”(《史记》)
道家、道教,说:①“按《荆山记》及《龙首记》,皆云黄帝服神丹之后,龙来迎之,群臣追慕,靡所追思,或取其几杖立庙而祭之,或取衣冠葬而守之。”(《抱朴子》)取衣冠葬,即“衣冠冢”。②“帝以土德王,应地裂而陟。葬,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黄帝登仙,其臣左彻者削木象黄帝,帅诸侯以朝之。七年不还,左彻乃立颛顼,左彻亦仙去也。”(《博物志》)③“(轩辕)帝升天,臣寮追慕,取几杖立庙,于是曾游处皆祠云。此庙之始也。”(《轩辕本纪》)轩辕,即姬轩辕,指黄帝。庙,即祖庙,指祭祖的建筑。“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中庸》)宗庙,即帝王的祖庙。礼,即礼制。祀,即祭祀。先,即祖先。
这些,都是对“中原文化-华夏文明”的追溯。历史学家,以《史记》为中华“正史”的第一部,而《史记》以给黄帝立传开篇,传到民间,便有了“有史自炎黄始”之说。道教是中华的本土宗教,脱胎于原始宗教,奉道家创始人老子为教主,是中华创世神话、中华原始民俗的守望者、继承者、光大者;因此,他们奉黄帝为道教之祖,为之立传,甘肃亦有类似记载。[10]据此,黄帝之世,即马家窑文化的那个时代,不仅有祭祖之俗,还有专供祭祀的祖庙、衣冠冢。正因如此,才会有“鬼罐”之说。
鬼文化,是祖先崇拜的产物,而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宗教的核心;因此,鬼文化是中华民族宗教的基础。信奉“万物有灵”、“人有灵魂”,是鬼文化的观念基础。萨满教的乌麦,是女娲的重要原型;因此,以乌麦为例,有助于了解鬼文化:
“按照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宗教学家泰勒《原始文化》的看法,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灵魂观念是一切宗教最重要、最基本、最古老的观念之一。灵魂问题是与人类同步的最古老的问题。萨满教普遍认为,灵魂源于上界神灵。在神话中,灵魂来自神灵,亦回归于神灵。乌麦(灵魂)住在天界乌麦神的神山或星座里,在那儿被神灵滋育,并从那里被派往氏族。当人死亡时,灵魂仍要返回到乌麦神国度里的氏族灵魂树上。人们普遍认为没有来得及长大成人的婴儿灵魂,会返回到创造它的乌麦神那里重新转生。传说,孩子长到一定年龄后,婴儿灵魂才转为成年人的灵魂。灵魂循环论是萨满教世界观中比较古老的观念体系,在这样的观念里,灵魂的循环往复取决于掌持生命大权和灵魂支配权的女神乌麦妈妈。借助司命神的发放与回收,灵魂周而复始与各类形体相合,使得万物生生不竭。”[11]
“人死曰鬼。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礼记》)“死者为鬼,鬼者归也。”(《韩诗外传》)“人所归为鬼。”(《说文解字》)“人死,魂魄为鬼。”(《正字通》)“人死为鬼,鬼死为聻。”(《聊斋志异》)“人死,精神升天,骸骨归土,故叫鬼。鬼者,归也。”(《论衡》)“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春秋传》)归,就是归属;厉,即厉鬼、恶鬼。所以,要安葬,要祭祀,让鬼魂安息。可见,最初的“鬼”并无善恶之别,泛指人的亡灵,即“人鬼”。后来,才把非正常死亡的,称作“厉鬼”。
土葬之俗,是如何兴起的呢?古人,说:“盖上古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因此,把尸骨装入彩陶,再埋入土,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俗信“多积阴德,天必报答”。
可见,让逝者安息,被先秦的圣人视作王道的象征。丧葬之礼,既是纪念祖先的宗教仪式,也是凝聚人心、巩固社稷、塑造民族的政治举措。祭礼衰,则人心散;人心散,则国祚短。因此,鬼罐之事,事关王道,不可不慎。考古学也好,民俗学也罢,应当撒播正气、褒奖良俗。
鬼罐既然关系到逝者,那么很可能是自己的远祖或与远祖沾亲搭故;因此,不宜过分强调彩陶的经济价值,应当尊重逝者,敬畏鬼罐。让逝者安息吧,别再拿彩陶去炒作、去赚钱,这些钱,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的道德标准来说,是作孽,而不是积德。
(2)制陶
彩陶文化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考古证实,马家窑人属于低地之羌、农耕之羌,即氐、氐族,他们所处的时空与炎帝、黄帝、蚩尤所处的时空大致接近,正是史前中华的繁荣期;因此,马家窑人拥有冠绝中华的彩陶文化。那么,为何把尸骨装入彩陶,然后土葬?
创世神话是民族文化的源头;离了它,我们讲不清民族的根。原始宗教是民族精神的源头;没有它,我们道不明民族的魂。原始民俗是民族特色的源头;缺了它,我们弄不懂民族的美。创世神话、原始宗教、原始民俗,是原始社会的文化三胞胎。根据这种内在联系,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家窑彩陶上的信仰。马家窑彩陶,作为制作精美的冥器,是人造的,而非天然的,显然寄托着制作者、使用者的精神追求。
人类社会,先是母系社会,以“采集-渔猎”为主,这是人类最古老的的经济类型,女子采集,男子狩猎,持续了数百万年,而随后的父系社会,至今还不到一万年。如此深厚的母系传统,怎会在以后的父系文明里毫无痕迹?陶器是第一种人造的石头,对于古人而言,是何等的神奇、自豪。为了礼赞,古人将陶器的来历挂在了女娲的名下,从而有了女娲制陶的神话,讲的是陶器的由来:
传说,女娲抟土造人之后,天下就有了人。有了人,就要使用家什,可是没有。人还不会造东西,只好还由女娲来造。造东西要样子(方言,即模型),没有样子如何造?女娲就拿女人的肚子做样子,造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圆不弄冬的容器,大的就叫缸、瓮、坛,小的就叫杯、盘、碗、盏。接着,女娲又照着小伲(吴越方言,意为小孩)撒尿的“小鸟”,把有些肚子样的容器也生上“小鸟”,那就是壶。你看,水壶、茶壶、酒壶。有了盛的没有盖的可不行,“肚子”不是露天了吗?女娲就照着女人乳房的样子做了盖子,乳头朝上刚好可以让手撮起来。[12]
“女娲捏黄土造人是中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天神女娲用黄土捏成了一个一个灵巧的活人,甚至用藤子搅拌泥浆,甩向地上,溅落的泥点也变成了人。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神话至少对应于两个史实:一是母系氏族社会成员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生育被神化了。二是其时人类已经能熟练地制造陶器。”[13]
“《物理论》曰:土精为石。”(《艺文类聚》)因此,古人在社坛前竖一块石头来象征“地母”女娲,她是社神之王、高禖。这块石头,史称“社石”、“高禖石”,俗称“女娲石”。
彩陶盆,是用泥土做的,腹鼓如孕妇,象征多产的地母神;因此,把尸骨装入彩陶,象征重新回到地母的怀抱,可得地母的庇佑,生死轮回。更何况,创世神话有女娲发明制陶之说。女娲是造人之神,身兼地皇,又发明了陶器,而陶器本身就是她对自己身体的模仿;因此,用陶器储藏尸骨,则可让女娲保佑鬼魂顺利地转世投胎。俗信,人骨是灵魂的居所;因此,二次葬便是收捡逝者的尸骨,然后装入罐子之类的冥器,再去埋葬。因此,这种陶罐实质上是棺材的演化。
“马家窑谱系的彩陶罐,器物体形演化的主线便是腹部逐渐圆鼓起来,到了半山和马厂类型时,器腹鼓起的程度达到了极限。当你站在那些无限圆鼓、数量难以统计的彩陶罐前时,你会对‘有容乃大’这个成语有更深刻的体会。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女们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做出无以‘腹加’的鼓腹容器,潜意识里指向的不是陶器的容量,而是借这无限鼓腹的陶罐,来歌颂母体伟大而神圣的再生能力。”[14]
俗信的“逻辑”是:既然人是土造的,因此哪里来、哪里去,去世后,施行土葬,讲究“入土为安”,即去世后,回到大地母亲那里去,以便来世投胎,再次做人。女娲,被奉为大地母亲、地母、地皇、地盘老爷、神州地祇、社皇、社王、后土,等等,都是大地崇拜的产物。后世,土地庙里供奉的土地,便是由此派生而来。因此,俗信逝者的鬼魂先要到“社庙-土地庙”去报到,然后由社神、土地这些神祇将其引导到“昆仑-泰山-丰都”。
“立冬日,朝廷差官祀神州地祇、天神太乙。”(《梦梁录》)“天子之社,祭畿内之地祇也。”(《礼记》。畿,即京畿,指王都之所在。)明·陆容《菽园载籍》说,“神州地祇”即京畿土地,指祭坛在京城的地神。所以,神州地祇是泱泱中华这个古老政权所辖范围内最大的地神。其社坛,是政府所立的最高等级的社,即太社,管整个神州。神州地祇的身份,往往与“人皇”重合,而堪称“人皇”者,首推女娲。“地祇,主昆仑也。”(《通典》)地之高者为山,万山之祖是昆仑。女娲造人,尽管有许多次,但只要提到地点,越古老的说法越会说是在昆仑山;因此,昆仑山是华人的发祥地,昆仑是华人的魂山。于是,“地神之王”女娲是昆仑山的主宰和象征,道家谓之“神州地祇”。
泰山,又写作“太山”,在神话观念里,即民族信仰里,它是昆仑山的派生,故有“泰山治鬼”、“泰山主死”之说;土地(神)是社神的派生,故有土地为冥神之说。“东岳泰山君,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师也,血食庙祀宗伯者也。”(《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序》)“晋巴丘县有巫师舒礼,晋永昌元年病死,土地神将送谒太山。”(《法苑珠林》)“俗谓土地为冥间地保,凡初亡者皆归此处,故丧事报庙、送行皆在土地祠。”(辽宁《海城县志》)“土地,俗称里社之神曰土地,人死往其庙押魂。”(河北《武安县志》)
如果说神话时代的马家窑彩陶离我们太远,不好理解;那么,信史时代的汉代画像砖石,则离我们较近,与前者同属“古羌文化-华夏文明”的范畴,都是“祭祀性丧葬艺术”,因此借助后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家窑的丧葬文化。[15]
(3)图腾
马家窑彩陶的象形图案,多种多样,但最基本的主题是生殖崇拜,而图腾崇拜则是生殖崇拜的阐释工具,是以象征语言来表达信仰。马家窑人所处的时代,尚属母系社会,人口的增殖是部族的头等大事;因此,男女性事被看得很崇高,从而使生殖崇拜成为主流文化。这种生殖崇拜,多半借助图腾崇拜来形象而生动地予以表达。
马家窑彩陶上的鱼、蛙,属于多产的动物,是生殖崇拜的对象,是龙图腾的原型。古羌认为人是“神龙”女娲所造,因此其后裔多称“龙的传人”。猴,跟蛇一样,是龙图腾的原型;因此,许多女娲造人神话的异文,讲的是女娲生猴子。
图1:从“女蛙”,到“女娲”;马家窑彩陶
古羌,即古氐羌,史籍统称羌戎、西戎、戎。羌(藏)语中的“戎”,意为低湿温暖的河谷。瑞纳,藏语仍称农耕之部为“绒巴”,巴即人。四川的汶川、茂县的现代羌民以及巫师们在大祭时戴金丝猴皮帽,以纪念取得粮种的猴祖师。在早期金文中,“戎”的汉字字形,是一位手执戈盾的武士形象。藏语、汉语的戎(狨),意为猿猴。羌、藏、汉都有传说:粮食种是猴子采摘来的。当今的博峪藏、文县白马人等部,农历五月要过“采花节”纪念此事。年节祭祖,要演傩戏《猴子生人》。[16]
太阳与火神之子的现代羌民、黄帝嫡派遗裔的白马人,生息在岷山。白马人傩祭是与火祭混同在一起的。甘肃文县白马人傩祭,在傩舞队之后,跟着一对脸上抹满锅烟的“公母猴”及一个“小猴子”。公猴、小猴,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角色,各身披一块破毡,头从毡中所挖的孔内伸出;母猴穿白马妇人的便装。傩队进入室内,公母猴便在追随的人群中肆意嬉闹,说着各种关于生殖的笑话,逗得围观的大姑娘、小媳妇们乐不可支。随即,在院中跳起《人与部落的由来》:初时,公母猴相互嬉戏挑逗,公猴作出种种可笑的姿态显示自身的雄强。终于,故作傲慢的母猴动情了,亲昵、交配,生下了小猴,即人。[17]
岷山北麓,兴起于白龙江畔的“猕猴种”党项羌,在宋初建立了以银川为中心的西夏国,与辽、宋鼎足而三。蒙灭西夏后,除少量逃归故土的党项,大部分融入汉人。至今,白龙江支流博峪河深谷中的博峪藏,是党项羌仅存的嫡裔,他们的女装仍保留了古赫羊国的图腾标示,红黑相间,抹胸用珊瑚,下有红肚兜,身后扎个大羊尾,保留了唐代赫羊国羌国的图腾风格,腹前有圆形装饰。[18]
纳西族,是古羌后裔,与史前的半坡村人、马家窑人,同源共祖,仍保留着图腾崇拜。“纳西族称猴为‘余’。第五代纳西先民称为‘初楚初余’,意为猴图腾的一代。在纳西族称谓中,称岳父为‘余普’,称岳母为‘余美’。余普,为公猴。余美,为母猴。这种称谓,典出东巴古籍《关死门经》。迪庆藏族自治州三坝纳西族在棺木头上要画一个白猴头。显然,
这一习俗说明去世了的那个人变成了猴子,即变成了祖先。死者入土后,纳西族说:‘素母日彪色,日科洛冷布,余科洛冷土。’意思是说,死者变成了蛇,从蛇洞送出去,又到了猴洞。纳西语‘余’,有两意,一为猴,一为过世俗生活。所以,所谓‘余科洛冷土’,意思是说,又将转世了。在纳西族的送魂路线中,有一站叫‘余足比吕柯’,意为猴子住的比吕柯。纳西族中源于猴氏族的人去世后,都要把死人的灵魂送到这一站,让死人的灵魂最终与祖先生活在一起。”[19]
图腾崇拜,本质上是生殖崇拜。图腾时代,俗信逝者需变为图腾,才能转世。因此,给彩陶绘上人面、图腾,是对逝者的超度,期盼其转世为人。超度,即期望鬼魂从阳间顺利到达阴间,再从阴间投胎到阳间,这个过程,需要超越、度过漫长的时空,故称。因此,马家窑彩陶上的鱼纹、蛙纹,往往跟图腾崇拜有关,表达了以“鱼”象征“龙图腾”、以“女蛙”象征“女娲”(图1)之类的神话思维。
二、人祖崇拜,定型甘肃
(1)人祖
女娲伏羲,被甘肃民间奉为“人祖”。华人的人祖崇拜,即对女娲伏羲的崇拜,定型于甘肃,光大于中原,而马家窑彩陶上的女娲、天水人祖庙的伏羲,尤其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