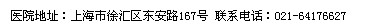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额窦炎 > 额窦炎诊断 > 著作理論及方法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
著作理論及方法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
什么医院能治疗白癜风呀 http://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著作、理論及方法:《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
趙成傑
摘要:《金石萃編》作為清代金石學史上舉足輕重的代表,既繼承了十八世紀重要的金石學理論和方法,又開創了新的學術傳統,為後世所仿效。以《金石萃編》成書前後為限,可以探究《金石萃編》在清代金石學發展中的重要貢獻。一方面考察其成書以前的金石學發展情況,尤其是乾嘉金石學者在金石學領域的著作、理論及方法;另一方面,《金石萃編》成書後清代金石學者又沿著《金石萃編》所開創的學術傳統,不斷發展。
關鍵詞:《金石萃編》;清代金石學;貢獻
清代金石學是中國金石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一時期從事金石研究的學者及著作要多於以往任何一個時代。從人數上看,陸和九《中國金石學》著錄清代金石學家位,宣哲《金石學人錄》則有位[1];從著作上看,林鈞《石廬金石書志》收錄清代金石著作種[2],容媛《金石書錄目》則收清人著作種[3],皆可看出清代金石學的繁榮。清代金石學的發展可以分成四個主要階段:清初以顧炎武、朱彝尊為代表,主張以金石服務經史;乾嘉時期步入清代金石學的發展階段,以錢大昕、王昶、翁方綱等人為代表;道咸以降,金石學的發展進入鼎盛時期,以何紹基、陳介祺為代表;晚清的金石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主要以楊守敬、葉昌熾、吳昌碩為代表。[4]《金石萃編》成書於嘉慶十年(),在此之前清代金石學著作雖數以百計[5],然而其所收碑刻數量、整理方法皆有可商之處。《金石萃編》“囊括包舉,文無不載,考訂無遺,上溯夏商,下迄遼元,足跡遍萬千餘里,收藏溯兩千餘年,積累至一千五百餘通。”[6]《金石萃編》開創了纂輯體的學術傳統,影響深遠。
[1]宣哲:《金石學人錄》(稿本),收錄於衛聚賢著《中國考古學史》,北京:團結出版社,年,第80頁。
[2]林鈞:《石廬金石書志》,《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年,第頁。
[3]容媛纂輯:《金石書錄目及補編》,臺灣:大通書局,年。
[4]郭名詢:《清代金石學發展概況與特點》,《學術論壇》,年第7期,第-頁。
[5]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史部·金石考古類》,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6](清)李祖望:《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序》,《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1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年,第—頁。
一、《金石萃編》成書前的清代金石學
(一)清初金石學的復興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對清初的金石學及《金石萃編》的編纂頗有影響。《金石文字記》凡六卷,自商代《比干銅盤銘》起,至《霍山廟建文碑》止,全書蒐集金石碑刻三百餘通,以時代先後為次,詳細標明金石碑刻所處的時代,是顧氏以二十年時間,遍歷天下名山、寺廟,并在前人金石研究基礎之上而完成的著作。《自序》云:“比二十年間,周遊天下,所至名山巨鎮,祠廟伽藍之跡,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其可讀者必手自鈔錄。得一文為人所未見者,輒喜而不寐。一二先達之士,知予好古,出其所蓄,以至蘭臺之墜文,天祿之逸宇,旁搜博討,夜以繼日,遂乃抉剔史傳,發揮經典,頗有歐陽、趙氏二氏之所未具者。”[1]由此可見顧氏在金石學上的努力,此後孫星衍、黃易、錢大昕等人亦都躬自親身,探訪金石碑刻。
《金石文字記》對後來金石學者的研究也有很大影響,主要有六:“一、發前人所未發;二、以經學為本,與史書等相發明;三、寓以守節之大義,貴古賤今;四、留心字樣之學,檢校諸碑別體字;五、寶重金石文字;六、書法觀。”[2]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對後代金石學著作產生了很大影響,不但開創了實學的風氣,扭轉了明末空疏的學風,還影響了錢大昕、王昶、翁方綱等金石學者的治學方向。李向菲《顧炎武與清初金石學的復興》對顧炎武的金石學成就進行了評價,她指出:“顧炎武在金石研究宗旨上,繼承了宋人考訂一路,又受時代風氣影響,在金石資料搜集上重可靠性和準確性,從而在治學態度與方法上對於清代金石學有決定性影響。這不僅僅是宋代金石考訂的重新提出,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宋人金石研究方法上的短處,使金石考據能夠走向深入。”[3]從《金石萃編》引顧炎武著作亦可看出王昶對顧炎武的重視,《金石萃編》引《金石文字記》(次)、《日知錄》(3次)、《山東考古錄》(1次)。[4]
清初金石學的復興,主要原因是明末以來訪碑傳統的接續。[5]經過清初學者努力之後,乾嘉金石學“又彪然成為一科學也”(梁啟超語),繼顧炎武《金石文字記》後,有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武億《金石三跋》、洪頤煊《平津館讀碑記》、嚴可均《鐵橋金石跋》、陳介祺《金石文字釋》,至王昶《金石萃編》“芸錄眾說,頗似類書”。無論從碑刻著錄的時限、地域範圍的廣度和深度,還是從事者之多,乾嘉時期金石學都是無以匹敵的。[6]
陸增祥《金石續編序》:“著录之家,本朝极盛,荟萃成书,奚啻百数。有限以时代者,有限以一省者,有限以一省並限以時代者,有限以一郡者,有限以一邑者,有限以域外者,有限以名山者,有限以一人者,有限以一碑者。有別以體者,有敘以表者,有繪以圖者。其上追秦、漢,下逮遼、金,近自裡閭,遠迄海外,綜括而考證之者亦不下數十家,或宗歐、趙之例,著目錄,加跋尾;或宗洪氏之例具載全文。或勘前人之訛,或補前人之不足。”[7]陸增祥對清代金石文獻著錄之豐富做了初步總結,乾嘉學者不僅對碑刻全文做了摹寫或著錄,還在前人基礎上作了更深入的研究。
(二)乾嘉金石學的著作、理論與方法
乾嘉金石學著作不下百種,內容上分為目錄、考證、纂輯三類;方法上則以歷史考證、書法鑒賞為主。錢大昕《郭允伯金石史序》:“自宋以來,談金石刻者有兩家:或考稽史傳,證事跡之異同;或研討書法,辨源流之升降。”[8]這一時期的金石研究呈現出“以金石證史”和“博採會稽”兩種不同的金石研究走向,并分別以《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和《金石萃編》為代表。《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清代金石學著作數以百計,主要著作如下表所示:
[1](清)顧炎武撰,徐德明點校:《金石文字記》,《顧炎武全集》第五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2]洪文雄:《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探析》,《書目季刊》,年第3期,第79-90頁。
[3]李向菲:《顧炎武與清初金石學的復興》,日本《東亞漢學研究》年特別號,第頁。
[4]趙成傑:《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第63頁。
[5]有關清初訪碑活動參見白謙慎著,孫靜如、張佳初譯:《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修訂版),北京:三聯書店,年。其他有關清初金石學情況可見張豈之:《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第四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年。
[6]暴鴻昌:《清代金石學及其史學價值》,《中國社會科學》,年第5期,第-頁。
[7](清)陸增祥:《金石續編序》,《金石續編》卷首,收錄於《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4冊,第頁。
[8]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冊,南京:鳳凰出版社,年,第頁。
本表所載為當時比較重要的著作,且不少著作在《金石萃編》中都有引用。金石學在清代的復興首先得益于最高統治者的重視,乾隆時期梁正詩編纂《西清古鑒》,仿《考古圖》及《宣和博古圖》體例將內閣所藏青銅諸器分類編纂,繼而又編纂《寧壽鑒古》《西清續鑒》等著作,自此上行下效“官方的著作、搜集工作帶動了私人著述的繁榮”[1]。《金石萃編》所處的時代正是金石學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金石學研究群體已由明朝遺老為主的研究者發展到維護清代統治的群體。乾嘉時期的金石學者大都在朝中擔任要職,不但學識淵博,還積累了深厚的人脈關係,如錢大昕、王昶、孫星衍、阮元、畢沅等學者。在金石尋訪、搜集、整理方面,王昶、阮元、畢沅都有自己的幕府,幕府中的學者協助其完成了金石的搜集整理工作。如阮元在乾隆五十八年()奉旨出任山東學政,這一時期的學術活動以金石學為主,與畢沅共同編纂了《山左金石志》。阮元《序》則交代了參與其事的學者:“引仁和朱朗齋(文藻)、錢塘何夢華(元錫)、偃師武虛谷(億)、益都段赤亭(松苓)為助。兗、濟之間,黃小松司馬搜輯先已賅備,肥城展生員(文脈)家有聶劍光(紋)《泰山金石志》稿本,赤亭亦有《益都金石志》稿,並錄之。”[2]有些學者同時為多個幕府編纂金石書,朱文藻除了協助阮元編纂《山左金石志》,還為錢大昕提供金石拓片若干;孫星衍也為阮元和王昶提供過金石拓片。[3]乾嘉金石學的繁榮得益於士大夫頻繁的職務調動與密切的學術交流,他們利用四處為官的機會,蒐集各地碑刻拓片,並為之題跋。學者間的金石交流廣泛且深入,涉及了碑刻互通、義例商定、題文跋尾、撰作碑誌、參稽有無等各個方面,充分體現出乾嘉金石學群體性、交融性、廣泛性的研究特點。
如表一所示,《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金石學著作表現出當時學者研究金石的三種不同傾向:第一類是著錄石刻目錄或只錄其文,間附考釋,即目錄之學,如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孫星衍《寰宇訪碑錄》()、錢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目》()等。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收錄自三代、秦、漢、魏、晉、六朝、隋、唐、宋、遼、金、元石刻,皆排比其目,注所在之地,所錄均為石刻[4]。此書尚有張馥庭抄本,《跋》曰:“黃小松司馬搜羅石墨不遺余力。此寫本碑目,上自三代,下迄元季,所藏最富。兵燹之後,不知拓本何在,而此書幸爲當歸草堂丁氏昆季購得,卷中率多小松先生手自標著者。”[5]黃易還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主要著錄和考釋漢代碑刻。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著錄周至元代碑刻余種,是書按年代排序,并標明地點、書體、立碑年月等,後人趙之謙、羅振玉、劉聲木皆有續補著作。[6]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目》著錄金石目錄二千余種,其中跋文者餘種。
隨著訪碑的深入,拓片也不斷增多,從清初曹溶《古林金石表》的余種,到孫星衍的余種,可以看出乾嘉時期的金石拓本在廣度上的擴大。在收錄金石的年限上,金石學者也注意到收錄下限過短的問題。如顧炎武鑒於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金石碑刻止收於五代,《金石文字記》則開始蒐集少量唐宋元題銘,這一點對王昶收錄碑刻有明顯影響。錢大昕云“予宋、元石刻愛之特甚”、孫星衍、武億、謝啟昆等人均收至於元[7],《金石萃編》亦收錄至元,兼及外國、南詔、大理石刻,收錄石刻下限的延長使金石資料更為豐富,客觀上反映了乾嘉金石學的繁榮。
第二類則專釋古碑文,即考證之學,如畢沅《關中金石記》()、褚峻《金石圖》()、翁方綱《兩漢金石記》()、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這一類著作在清代金石學史上比重最大,其中《關中金石記》專收陝西地區自秦至元碑刻,凡種,較朱楓《雍州金石記》多出種。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自關內、河西、山南、隴右悉著于錄,而且徵引之博,辨析之精,沿波而討源,推十以合一,雖曰嘗鼎一臠,而經史之實學寓焉。”[8]此書的實際編纂者是孫星衍,孫氏還協助編纂了《中州金石記》。乾隆六十年前後,孫星衍、阮元、畢沅同在山東,先後編著了《關中金石記》《中州金石記》以及《山左金石志》等著作。
《金石圖》由褚峻摹圖、牛運震補說,收錄漢代碑刻種,此書的編纂受顧炎武影響,“其所收,則近循顧寧人先生《金石文字記》例,非親見而手摹者,不著於錄。詳其在所,斷自周秦,以迄季漢,為其尤易殘滅也。而審定為重勒者,則逸焉。”[9]褚峻不但摹寫碑刻、縮印拓片,亦一一指出碑刻行款尺寸及所在位置。《金石圖》的貢獻不在考證,主要開創了碑刻摹圖之法。將碑刻全文影寫在紙上,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類似褚峻《金石圖》、馮雲鵬《金石索》等將碑刻全圖影寫,亦稱翻刻法(reprintmethod),即按照原拓本重刻。這樣的好處是保存了拓本原貌,缺點是佔用紙張空間,有些碑刻僅存數行,卻要將整葉全部附上,既佔用空間,又不美觀,而且不方便刻工排印,於是產生了另一種摹寫法——雙鉤(doublehookmethod)。雙鉤法將全文重新摹寫,顧炎武《求古錄》、陳奕禧《金石遺文錄》、吳玉搢《金石存》、王昶《金石萃編》等皆是此類。以《金石萃編》為例,為了避免原拓失真,《金石萃編》採用原字體摹寫模式,如《散氏銅盤銘》按金文字形摹寫、《嶧山刻石》按小篆字形摹寫、《泰山都尉孔宙碑》按隸書字形摹寫、《始興忠武王碑》按楷書字形摹寫,如遇不識之字或闕文以“囗”代之,凡文散見多處者,採用旁注以記其全,篆隸及古文別體字,都摹其點畫,加以訓詁,題於額陰兩側。《金石萃編》以原字體摹寫,很好地避免了原拓失真,並且節省空間、方便編排。雖然清初學者如王澍、吳玉搢、金農等人已使用雙鈎法摹寫,但並未普及,仍以翻刻法為主。雙鈎摹碑法一般認為在清中葉開始流行,以翁方綱、黃易等人為中心,如《淳於長夏承碑》《李翕西狹頌》《博陵太守孔彪碑》等均是用此法勾摹,直到晚清石印術傳入中國用此法勾摹碑刻方才絕跡。[10]
再如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是書錄兩漢碑刻,凡種,附魏、吳、晉碑刻10種。此書的珍貴之處在於作者以手拓目驗方式確保碑刻來源的可靠性,他強調:“方綱謹録漢碑之字,惟據拓本録之。其必不得已,或有據摹本者,更有必不得已而據著録者,則亦十無一二耳。”[11]翁方綱的金石研究側重于書法鑒賞,如《孔廟禮器碑》:“然愚之論碑惟以字體爲主。今觀右側與前筆勢尚相近,而左側益横肆不羈,蓋由右而左正變備矣。”[12]上海圖書館還有葉景葵跋本,曰:“此龔孝拱校本,凡總目加墨點者,均以原石拓本或名家鈞刻本校讀,精審之至。前見所校《劉熊碑》翁跋,詆訶不少假借。此書雖亦訾翁之不學,而于其論書之精語則傾倒備至。孝拱善讀書,蓋非信口雌黃者。”[13]
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收錄金石考證文字種,對《金石萃編》的編訂產生了重要影響。錢氏強調以金石證史,將石刻文獻作為研究材料,側重“經史”,而非石刻本身。此書將金石的收錄範圍擴大到宋、元、遼、金、明,而不膠固於歐陽修《集古錄》以五代為限。王鳴盛《跋尾序》:“予嘗論其完備者凡六家:自歐陽外則趙氏明誠、都氏穆、趙氏崡、顧氏炎武、王氏澍,斯為具體。而以跋入文集者,如曾氏鞏、歸氏有光,寥寥數通,未足名家。惟朱氏彝尊始足並列為七焉。最後,予妹婿錢少詹竹汀《潛研堂金石跋尾》,乃盡掩七家出其上,遂為古今金石學之冠。”[14]王鳴盛所列七家: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都穆《金薤琳琅錄》、趙崡《石墨鐫華》、顧炎武《金石文字記》、王澍《金石文字必覽錄》以及朱彝尊《曝書亭金石跋尾》,此七家共同特點皆以“跋尾”為研究重心,錢大昕摹法七家,後出轉精,錢大昕《跋尾》之後,仿其體例,考證金石者眾多,如武億《授堂金石跋》、阮元《山左金石志》等皆為此例。
武億在金石學方面有多部著作傳世,《金石三跋》收錄金石跋文則,《授堂金石文字續跋》收錄則,此外還有《偃師金石遺文記》《安陽金石錄》等著作。他的金石考證側重以金石考證經史,將金石文獻作為經史典籍的補充,并通過金石文字與傳世典籍的對校訂正典籍在流傳過程中的錯訛,體現了乾嘉金石學的主流治學方法。[15]阮元在金石學方面貢獻突出,所撰《山左金石志》()不再局限于石刻,也包含了青銅器、錢幣、璽印等質材,凡0餘通,從收錄範圍和數量上與《金石萃編》大體相當。此書特色乃是“錄金石而分地”,專錄山東地區金石文獻,孫星衍、黃易、翁方綱均為此書提供了金石拓本。
第三類為纂辑之學,如李光暎《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吳玉搢《金石存》()等著作。《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成書于清雍正七年()[16],該書凡十六卷,著錄金石碑刻通,引錄各類資料餘種,採集金石家之書40種,文集、地志、說部之書又60種[17],按語以“光暎識”結尾。李遇孫認為李光暎的《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為《金石萃編》之先聲。[18]從體例上說,是書先引諸書,末附按語,但按語不足十分之一,如卷七《晉祠銘》分別錄《石墨鐫華》《墨林快事》《曝書亭集》《金石文字記》以及李光暎識語等;在考證方面,以品評書跡為主,不似其他著作以考證史事為長。吳玉搢《金石存》收錄金石文字種,前三卷為篆書,後十二卷為隸書,採用雙鉤法摹錄碑文。是書只收篆隸,不錄行楷,該書成書于乾隆三年(),所錄皆為作者所見。《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金石纂輯之作並不多見,但在《金石萃編》成書以後,各家皆以其為準,爭相仿效。
《金石萃編》成書以前的清代金石學在分類上較為單一,目錄、考證以及纂輯著作成為主流,類似專輯性質的璽印、瓦當著作尚未形成系統,收錄也較為零散;考證類著作多是跋尾形式,金石學家多通過手拓目驗方式著錄金石文字,形成了幕府士人專門從事搜集、整理金石的編纂方式;在學術方法上,主要以歷史考證和書法鑒賞為主。[19]《金石萃編》成書後,乾嘉金石學的主流變成了以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為代表的“跋尾類”著作、以王昶《金石萃編》為代表的“纂輯類”著作和以翁方綱《兩漢金石記》為代表的“鑒賞類”著作。[20]其中,“跋尾類”著作數量最大,武億、阮元、黃易、畢沅、孫星衍等人的跋尾著作多達數部,這類著作常伴隨金石目錄類著作,不少題跋就是對金石目錄的再整理,如錢大昕有《潛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黃易有《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小蓬萊閣金石目》等;“纂輯類”著作主要以《金石萃編》續補著作為主,大都仿照其體例,補充金石材料,擴大收錄範圍,吳榮光、瞿中溶、陸增祥等學者所撰的續補著作就是對《金石萃編》學術傳統的繼承;“鑒賞類”著作專門比較拓本的訛舊、存字的多少,關鍵點畫的完缺以及書法特點的評價,朱彝尊、王澍、黃易以及後來的趙紹祖、何紹基等金石學者都有將金石與書法鑒賞相結合的實踐。翁方綱提出金石的鑒賞不同於經史考證,主張把書法風格、宗派源流的考察與具體的字形體勢、筆意特征相對應,既不可“虛言神理而忘結構之規”,也不可“高談神肖而忽臨摹之矩”。[21]
王昶《金石萃編》以及續補著作開創了新的學術傳統,在清代學術史上也是立意深遠的。在王昶之前的清代金石學者,或以撰作金石目錄、擴大收錄範圍為學術傳統,如孫星衍《寰宇訪碑錄》及其續補著作;或考證金石以證經史為學術傳統,如錢大昕、武億、黃易的題跋類著作,他們強調“以金石證史”,目的通過金石文獻與傳世典籍的對讀來訂正文獻的訛誤。這三種學術傳統構建成了清代金石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在《金石萃編》成書以後,金石學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學術傳統不斷延伸,呈現出立體化、系統化的研究趨勢。
[1]馬洪菊:《葉昌熾與清末民初金石學》,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年,第37頁。
[2]阮元:《山左金石志序》,《山左金石志》,收錄于《續修四庫全書》第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3]張俊嶺:《朱筠、畢沅、阮元三家幕府與乾嘉碑學》,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年,第頁。
[4]徐憶農:《南京圖書館藏稿本小蓬萊閣金石目》,《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年,第頁。
[5]陳先行、郭立暄:《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年,第頁。
[6]王鍔:《寰宇訪碑錄及其補作》,《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年第1期,第22-25頁。
[7]宋凱:《金石萃編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年。
[8]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冊,南京:鳳凰出版社,年,第頁。
[9]湯劍煒:《金石入畫:清代道咸時期金石書畫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38頁。
[10]趙成傑:《物質形態的轉化:訪碑背景下的金石圖書寫》,《南京藝術學院學報》(美術與設計),年第5期,第28-30頁。
[11](清)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三《漢石經殘字》,收錄于《續修四庫全書》第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12]《漢石經殘字》,第頁。
[13]陳先行、郭立暄:《上海圖書館善本題跋輯錄》,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年,第頁。
[14]《嘉定錢大昕全集》(增訂本)第九冊,第頁。
[15]朱添:《武億與乾嘉金石學》,黑龍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年,第頁。
[16](清)李光暎:《觀妙齋金石文考略》,雍正七年()刻本,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17](清)翁方綱纂、吳格整理:《翁方綱纂四庫提要稿》,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年。
[18](清)李遇孫著、桑椹點校:《金石學錄》,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年,第61頁。
[19]李峰、王記錄:《中國古代的金石學研究與文獻考證》,《歷史文獻研究》第35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年,第—頁。
[20]劉恒:《中國書法史》(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年,第頁。
[21]馬新宇:《清代碑學研究與批評》,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年,第33-34頁。
二、《金石萃編》成書後的清代金石學
《金石萃編》成書以後,清代金石學迎來了道咸時期的鼎盛。相關金石著作不斷湧現,除了本文已列有關《金石萃編》續補著作外,還出現了數以百計的金石目錄、考證、題跋之作,相關拓本的單篇題跋更是不計其數。按照時間來分,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道咸以降,金石學的研究範圍明顯擴大,研究內容也豐富廣泛。[1]
[1]有關清代中後期金石學的研究前賢已經論述較為詳細,如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朱劍心《金石學》、周睿《儒學與書道——清代碑學的發生與建構》、湯劍煒《金石入畫:清代道咸時期金石書畫研究》、王弘理《中國金石學史》以及各類金石學、書學著作均有提及,上述著作多從金石學收錄範圍、金石學研究內容等角度入手展開研究,不少專著以金石學家為中心,如陳介祺、葉昌熾、阮元、畢沅、黃易、翁方綱、趙之謙等金石學家皆有專論,言其金石學成就必論清代金石學之發展及其演變,可謂汗牛充棟。
这一時期的金石研究開始向專門化延伸,形成輯佚、考據、鑒賞相結合的研究特點,以何紹基、陳介祺為代表。第二階段是晚清時期,其特點是開始走向總結階段,葉昌熾《語石》總結了金石學的若干義例,主要以楊守敬、葉昌熾、吳昌碩為代表。《金石萃編》成書以後的清代金石學著作數以百計,主要著作如下表所示:
《金石萃編》成書後的清代金石學呈現出以下三個發展特點:
第一、金石義例類著作逐步成熟,并出現如《碑版文廣例》《語石》等總結性著作。王芑孫的《碑版文廣例》為補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而作,《自敘》云:“吾今於潘氏、王氏所已舉不更舉,其所未舉一一舉之。潘氏、王氏專舉韓、歐,吾一不舉韓、歐,要之以文章正統與韓歐也。”[1]此書凡十卷,前六卷皆是對漢碑碑例的舉證,如卷三《以文為誄以頌為敘例》《碑後附記他人行事例》等,再如卷七《題額人列名所始例》:“自漢迄隋唐,書人撰人各自有見,從無書額人姓名見於碑中,有之自《孔子廟堂碑》始。”[2]當然金石義例的總結主要為了考訂史實,王芑孫認為金石義例對古文創作也有一定益處。王瑬《碑版文廣例敘》:“學古文者,當始由無例以之有例,繼由有例以之無例。”[3]葉昌熾《語石》的問世標誌著金石義例之學的成熟與完備,《自序》言此書“上溯古初,下迄宋元,玄覽中區,旁徵島索。制做之名義,標題之發凡,書學之升降,藏弆之源流,似逮摹拓、裝池、軼聞、瑣事,分門別類,不相雜廁。”[4]《語石》總結金石義例條,則,如卷三《論碑之名義緣起》論述碑之名義:“碑與文字刻石,本是兩事。碑者,所以麗牲引繂,初無文字。古人紀事垂後,類皆銘刻器物,吉金欵識為多。間刻於珪璋者,已為最初之石文,然不抵金文千百分之一。”[5]再如卷七主要討論古代刻工,《總論南北朝書人》:“隋以前碑版,有書人名可考者,南朝以陶貞白為第一,貝義淵次之。北朝以鄭道昭為第一,趙文淵次之。其餘南之徐勉,北之蕭顯慶、王長儒、穆洛、梁恭之,皆入能品。”[6]《語石》不僅在寫作宗旨上不同於其他著作,在論述範圍上也不局限於傳統碑、志,對其他形質的石刻也有涉及。[7]
第二、金石目錄學的總結性著作開始出現,乾嘉時期金石目錄之作以《寰宇訪碑錄》為最,道咸以降,吳式芬《攈古錄》收碑刻種,加之磚瓦、木類、玉類等,共計種。書中所收金類悉錄原文、收藏者姓名,惟不載璽印、泉幣;石類則磚瓦之屬悉錄原文,石刻皆詳記書體和年月日,及其題類書體碑陰諸刻,並說明屬在某地,藏於某人;其他據摹本列入者,亦說明從某書或某人摹本,其中有誤釋誤記者,亦隨目加以訂正。[8]《攈古錄》收集金石豐富、考據精審嚴謹,《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其“凡吳式以前,各家金石并錄之目,從未有如此且詳且備者。”[9]晚清學者繆荃孫在金石目錄的編纂上也有多部著作問世,《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藝風堂金石文字續目》《再補寰宇訪碑錄》《金石分地編目》等。[10]《藝風堂金石文字目》收錄金石10種,以石刻為主,以時間為序編排,并以注語形式指出碑之鐫刻時間、地點、撰者等。[11]
吳式芬、繆荃孫的金石編目更加注重對學術傳統的繼承,學界對孫星衍《寰宇訪碑錄》的補充和訂正成為清代金石學的另一個學術傳統,吳式芬明確提出,其所撰《金石彙目分編》是為補《寰宇訪碑錄》而作。《自序》:“其間薈萃諸家總為目錄者,惟孫伯淵《寰宇訪碑錄》一書,最為大備。惜乎條目重複,釐剔未能淨盡,時地不免舛誤。”[12]吳式芬之後有趙之謙《補寰宇訪碑錄》,收錄秦至元的碑刻餘種,繆荃孫《再補寰宇訪碑錄》又補餘種,劉聲木《續補寰宇訪碑錄》以及羅振玉《再續寰宇訪碑錄》等著作都是對《寰宇訪碑錄》學術傳統的繼承。
第三、將金石研究與書法創作有機結合,形成金石考證、書畫鑒賞相結合的研究模式。金石學的發展與文字學、藝術學密不可分,關注焦點由對傳統金石文獻的整理和考證向書法、繪畫的藝術品鑒過度。何紹基、趙之謙、包世臣等學者的書法創作都與傳統金石息息相關。黃賓虹《自題江村圖》:“逮清道咸金石學盛,籀篆分隸,椎拓碑碣精確,書畫相通,又駕前人而上,真內美也。”[13]湯劍煒進一步總結為:“道咸的繪畫具有強烈的金石意蘊,從筆法到意境,甚至內容都有金石的影子……道咸開創了從北碑和篆隸而來的新筆墨體系,在筆墨的結合度、書法篆刻的配合度方面都前所未有。”[14]趙之謙作為清代中後期的代表人物,曾撰作《二金蝶堂印譜》《六朝別字記》《補寰宇訪碑錄》等著作,金石書法入畫是其書畫創作的重要特點。
[1](清)王芑孫《碑版文廣例》,朱記榮輯:《金石全例(外一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年,第5頁。
[2]《碑版文廣例》,第頁。
[3]《碑版文廣例》,第4頁。
[4](清)葉昌熾、柯昌泗:《語石語石異同評》,北京:中華書局,年,第1頁。
[5]《語石語石異同評》,第頁。
[6]《語石語石異同評》,第頁。
[7]馬洪菊:《葉昌熾與清末民初金石學》,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年,第頁。
[8]孫才順:《吳式芬與金石學》,《齊魯文化研究》,年第2期,第-頁。
[9]傅璇琮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10](清)繆荃孫著;張廷銀、朱玉麒主編:《繆荃孫全集·金石》,南京:鳳凰出版社,年。
[11]楊洪升:《繆荃孫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頁。
[12](清)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第2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年,第頁。
[13]黃賓虹:《黃賓虹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年,第50頁。
[14]《金石入畫:清代道咸時期金石書畫研究》,第頁。
三、《金石萃編》在清代金石學史上的貢獻
《金石萃編》是乾嘉時期承上啟下的一部著作,不但充分吸收了前人的重要成果,還在此基礎上有了新的探索。《金石萃編》開創的學術傳統縱然被後世著作所吸收,但重要功績遠不止於此,王昶的訪碑、拓本的甄選、碑刻的編排、金石書的選擇以及按語的撰寫都對以後的金石學著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王昶藉助為官之便,廣泛交遊,以王昶為紐帶,連接著清代金石學、文字學、歷史學、考據學的重要學者。另一方面,《金石萃編》也存在許多不足,前人除了訂正、補充以外,還對碑文義例、金石真偽多有辨正。以上都是《金石萃編》對清代金石學的作用,但同時也應看到清代金石學對《金石萃編》的回應。
《金石萃編》成書後,眾多金石學家群起而效仿之,不但吸收了《金石萃編》的理論、方法,還不遺餘力地校勘、批註、考證,形成眾多批校本的同時,也將王昶的文學、小學、歷史學與金石學結合起來綜合考察,呈現出乾嘉時期金石學繁榮的新氣象。吳泰來《春融堂集詩序》引王昶語:“吾之言詩也,曰學,曰才,曰氣,曰聲。學以經史為主,才以運之,氣以行之,聲以宣之。四者兼,而弇陋生澀者庶不敢妄廁於壇坫乎。”[1]王昶論詩講求學、才、氣、聲四者兼備,又以學、才為根底。學指經史,正與翁方綱“肌理說”相呼應;“才”指作家個性,是對袁枚“性靈說”的借鑒;而“音”指格律,是對沈德潛“格調說”的繼承。
王昶在《春融堂集》中撰寫了一定數量的論碑詩,如《題高氏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後》有“摩挲望古莫深喟,聊與繡閣供臨摹”,小字注為:“碑載前濮州鄄城縣林諤撰,朝議郎、太原府司錄參軍常山蘇倇題額,太原府參軍房嶙妻渤海高氏書。寺在西山石壁谷,太宗文德皇后過此不豫,禮佛而愈,更為修建。開元間,邑宰燉煌張某增葺之,僧灌潤等又鑄鐵彌勒像一軀,修諸好相,故為頌銘。”[2]此碑收錄於《金石萃編》卷八十四,記述了造像頌的撰者、書者以及修鑄經過;再如《題潭州鐵佛寺塔柱文後》小引有:“《潭州志》:‘唐開元時,衡岳降神,舍鐵造佛,兼以鑄塔。’乾隆四十年,梁階平中丞國治修寺,工畢,次及,除舊甓,得鐵柱如幢贯塔中,長丈有四尺,圍尺有八寸。上刻觀察李思明皈依慈氏,發願生內院文。下刻陀羅尼呪,皆宋淳化元年進士董頀書。僧曰道崧,工曰李昇,计字七百六十有奇,完好可诵。臬使梁幼循敦書搨以遺余,且屬作詩以記之。”[3]這段記載收錄到《金石萃編》卷一百二十五中,文字稍有不同。另外,《春融堂集》所錄《夏太常墨竹為松崖上人題》《樊秀才贈瘞鶴銘》《天發神讖碑》《嶧山》均以詩歌形式考證碑文。王昶的題碑詩將詩歌創作與金石題跋融為一體,使冰冷的金石栩栩如生,從這個方面也表現出王昶論詩重視“學、才”的特點。如《過大理驗緬人貢物,提督烏君大經留飲園亭,有作》:“南金象齒見蠻官,軍府招留竞日歡。十載聲靈员赫濯,三宣耕鑿永平安。人如萍梗谁能定,迹讬苔岑别亦难。痛飲還須澆大斗,醉聽座下響飛湍。”[4]王昶赴雲南做官,途經大理與提督烏大經飲酒,亭下有泉水激流,作詩以記。王昶在詩作中或描繪訪碑之難,如《題何上舍夢華得碑圖》:“此碑之出本何所,乃於孔廟危墻側。沙礫紛披雜苔蘚,杉楠颯沓樷剂棘。”[5]或記述碑文行款,如《觀魏大饗受禪二碑》:“吾見此文亦已久,朅來親讀披蓬蒿。三十二行行款正,加以隸體無殘凋。”或表達對碑刻的傾慕,如《永明林明府昆瓊以澹山石刻見示》:“澹山本澹遠,疑是神仙居。我常慕其勝,寤寐時縈紆。”[6]
王昶書信中常涉金石考證與評價,或表達自己的金石主張,如《與錢辛楣》:“竊意墨刻之書,須仿洪丞相《隸釋》例,備載全文。然後將古今作者,如《集古錄》《金石錄》《鐵綱珊瑚》《金薤琳琅》《石墨鐫華》諸書所有考證、辨論悉行采入,附於各通之後,始為墨刻集成。”[7]或對當時金石學的評價,《與張遠覽》:“碑版之學,近來惟錢學士大昕、吳學博玉搢最為博洽。中州人士,端賴年兄。”[8]或鼓勵後輩撰作金石書,《與沈果堂論文書》:“今之學者弗參互考訂,而潘氏《金石例》、王氏《墓銘舉例》等書,世亦不復傳習,是以雖號為能文詞者,每有作輒繆鰵不合於古。足下本經術,為文以迪後進,又所居松陵王寅旭、潘稼堂兩公遺澤未艾,必有好古能言之士出焉。”[9]或述其訪碑見聞,《與錢沖齋書》:“頃過廣通,入飛來寺,見有碑陷壁間,蓋明按察司副使池陽沈某書,書中涓剏寺颠未甚具。”[10]或論碑文書跡,《覆倪敬堂書》:“唐人於右軍,似而不似,不似而似,如汝南公主、實際寺靈運禪師,皆有右軍一體。即《明徵君碑》筆意,亦出於王,特參以褚法,稍加展拓。”[11]《又倪敬堂書》:“高宗真是右軍法乳,欲學《蘭亭》《聖教》《薦福寺》者,非此無以入門。太宗好右軍,筆力矯然,若其純熟處,或遜於高宗。自來書家於金石文字,不能旁搜博采,故知高宗者绝少耳。”[12]王昶的書信涉及金石討論的內容非常廣泛,他在編纂《金石萃編》之前就有非常深厚的學術積累,不但與前輩交流討論,還常獎掖後學,由此產生的金石學著作亦可視為王昶對清代金石学的贡献。
[1](清)王昶著,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年,第6頁。
[2]《春融堂集》,第19頁。
[3]《春融堂集》,第頁。
[4]《春融堂集》,第頁。
[5]《春融堂集》,第頁。
[6]《春融堂集》,第頁。
[7](清)王昶著《履二齋尺牘》,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抄本。
[8]同上。
[9]《春融堂集》,第頁。
[10]《春融堂集》,第頁。
[11]《春融堂集》,第頁。
[12]《春融堂集》,第頁。
感謝趙成傑研究員賜稿,本文據其新著《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修訂首發。
趙成傑(—),黑龍江寧安人,南京大學文學博士,韓國首爾大學中文系博士後,現為雲南大學歷史與檔案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尚書》學、說文學、金石學及傳統文獻整理與研究。已在《文獻》《中國典籍與文化》《書目季刊》《嶺南學報》《福建論壇》《國際漢學》等海內外期刊發表論文五十餘篇,出版專著兩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項,主持博士後基金項目三項,入選“博士後國際交流計畫派出項目”。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年:-5-1
頁數:
定價:.00元
《金石萃編》在金石學發展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首先該書彙集了西周以來重要的金、石拓本,以“石”為主,為後世學人翻檢、查考提供了便利;其次,以《金石萃編》為中心的續書、補書不斷湧現,逐步構建起清代金石學大廈。對《金石萃編》及續書、補書的研究不但有利於考察《金石萃編》本身的學術價值,亦有益於對整個清代金石學史的把握。本書採取文史結合的方法,從文獻文化史的角度,將《金石萃編》作為一部學術經典,一種研究範式,進行了全面系統的研究。
緒論
一、王昶生平與學術
二、學術史的回顧與展望
第一章《金石萃編》成書前的清代金石學
第一節《金石萃編》及其時代
一、乾嘉考據學的學術背景
二、《金石萃編》成書前的清代金石學著作總覽
第二節王昶事蹟、著述及交遊
一、王昶事蹟釋疑
二、王昶著述補考
三、王昶與乾嘉金石學者之交遊
第三節王昶的金石尋訪與收藏
一、王昶本人的金石蒐訪
二、親屬、僚友、門人的拓片交流
第二章《金石萃編》編纂成書考
第一節《金石萃編》協助編纂考論
一、朱文藻及其協助編纂
二、錢侗及其協助編纂
三、王濤及其協助編纂
四、陶樑及其協助編纂
五、彭兆蓀、史善長等人與王昶著作編纂
第二節《金石萃編》的編纂特點
一、目錄及其特點
二、存文及其特點
三、集釋及其引書
四、考證及其貢獻
第三章《金石萃編》引書考
第一節引書數量及名稱
一、引書概況
二、引錄單篇文章及跋文概況
第二節引書體例與特點
一、引書體例及其間關聯
二、引書特點及相關問題
第三節引書貢獻及意義
一、引書貢獻
二、引書意義
第四章《金石萃編》續補考
第一節《金石萃編》續補分類
第二節《金石萃編未刻稿》及相關著作
一、《金石萃編未刻稿》
二、朱文藻《金石補編》
第三節續補存目之屬
一、黃本驥及其《金石萃編補目》
二、許槤及其《金石補編目錄》
第四節續補校訂之屬
一、羅振玉及其《金石萃編校字記》
二、羅爾綱及其《金石萃編校補》
三、魏錫曾及其《金石萃編刊誤》《績語堂碑錄》
第五節續補補遺之屬
一、《八瓊室金石補正》之編纂及其體例
二、《八瓊室金石補正》之意義
三、其他續補《金石萃編》著作
第五章《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之構建
第一節《金石萃編》刊佈與流傳
一、《金石萃編》的主要刻本和批本
二、《金石萃編》成書後的傳播情況
第二節《金石萃編》對清代金石學的學術影響
一、道咸以後的清代金石學發展脈絡
二、《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的學術聯繫
第三節《金石萃編》在清代金石學上的學術地位
一、《金石萃編》續補著作之優劣得失
二、《金石萃編》續補著作在清代金石學史上的貢獻及意義
三、由《金石萃編》引書所見清人治金石之特點
四、《金石萃編》對奠定清代金石學格局之影響
結語
《金石萃編》引書情況總表
《金石萃編》按語集萃
主要參考文獻
本書各章發表情況
後記
附:程章燦先生《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序》
作為一門學問,金石之學興起於趙宋之世。此前雖然也有對於金石刻辭的載錄、引證與研究,但都是零星的保存與利用,並未形成一門自覺而系統的學問。從北宋開始,以歐陽脩《集古錄》和趙明誠《金石錄》等書的出現為代表,金石之學經由宋代文士手中,被逐漸培育成一門富有文人趣味的學問。隨後的南宋時代,又有以洪适《隸釋》《隸續》、陳思《寶刻叢編》及佚名《寶刻類編》等書為代表的一系列金石學著作相繼湧現,使這門學問日益充實增廣,不僅端居學問殿堂之上,而且擁有顯著的地位。歐、趙、洪、陳等人的著作,以各自不同的結構、各具特色的旨趣,奠定了金石學的規模和基礎,也指示了此後金石學發展與提升的多種可能與方向。
宋代金石學的成立,既反映了當時士人優游文藝、好古博雅、玩物成癖的生活形態,也反映了與當時經學、史學等學科發展密切相關的文化學術生態。宋代經學中疑經辨偽的學風,直接影響並且促進了金石學的發展,而金石學的發展,又從史料、史法乃至史識等方面,促進了宋代史學的發展。當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對宋代史學的評價極高。他曾經提出:“中國史學,莫盛於宋”,“有清一代經學號稱極盛,而史學則遠不逮宋人”。陳寅恪先生的這一論斷,在當代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先師程千帆先生也非常認同這一觀點。年,筆者報考程千帆師的博士研究生,考題中就有一道要求評述陳先生此說,故而印象尤其深刻。毋庸諱言,金石學是臻於極盛的宋代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在兩宋三百年的歷史中,金石學形成了包括著錄(如《集古錄》《金石錄》)、存文(如《隸釋》《隸續》)、賞鑒考證(如《集古錄跋尾》)等在內的學術體系,它不僅顯著拓展了歷史研究的史料視域,而且開啓了藝文賞析、史學考證以及拓本玩賞等多種文藝與學術相互為用的門徑,為文學、歷史以及藝術等多學科研究的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啓示。從這些角度來說,宋代金石學可以說是盛況空前的。
清代史學固然總體上“遠不逮宋人”,但是具體到清代史學的每個具體門類,卻不能說它們全都“遠不逮宋人”。例如,與宋代金石學相比,清代金石學並不遜色。清代的文士生活形態當然不同於宋代,但玩賞金石之風更盛於宋代,這種風氣瀰漫於士人圈,成為士人交際之時最基本、最通用的共同語言之一,這是促進清代金石學發展、大量金石學著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的主要社會土壤。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一些社會地位較高的金石學家,如王昶、畢沅、阮元等人,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可以調動較多的人力、物力資源,組織大規模的金石尋訪,完成大型金石著作的編纂。與此同時,清代的經濟發展水平,也為金石尋訪和拓本製作提供了比宋代更為有利的物質條件和交通條件。另一方面,清代學術特別是乾嘉考據之學的繁榮,又將考證之學由經史而蔓衍至金石考證,為清代金石學奠定了學術的根基。錢大昕所撰《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不僅是一部史學名著,也是一部金石考據名著。在這部書中,他自覺地利用石刻史料與歷史文獻相互比勘,考證諸史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創獲頗多。實際上,這可以說是王國維所提倡的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的先驅。
如果說錢大昕《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代表了清代金石考據之學所達到的專業精深的高度,那麼王昶《金石萃編》則代表了清代金石目錄的集成博大的氣象。《金石萃編》的出現,不僅是金石學發展到清代的集大成之作,也是乾嘉學術的水到渠成之作。此書之成,累積五十餘年之功,傾注二十餘人之心力。作為一部金石目錄之書,它在體例上融合眾長,在文獻上廣徵博引,使之成為同類著作中更精、更全、更大之書。當然,《金石萃編》一書中仍然存在不足,在隨後出現的各種《金石萃編》的續補、校正之書中,這些不足得到了補正。這些續補著作層出不窮,不一而足。具體而言,又可以分為存目、校訂、補遺三大類,它們不僅在清代金石學著作中自成系列,並且以《金石萃編》為中心,構成清代金石學的一個學術傳統,從而進一步確立了《金石萃編》作為金石學經典的地位。因此,要更好地認識王昶及其《金石萃編》的學術貢獻及其歷史地位,不僅要從成書過程、體例設計等常規的文獻學視角切入,而且要重視此書的傳播與接受,將此書置於其所處的學術傳統中加以考察。換句話說,不僅要從書的本身,而且要從書的周邊來考察這部金石學名著。——這正是趙成傑博士新著的特色之一。
我與成傑認識,始於年。那年8月,我應邀為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舉辦的古文獻學暑期學校授課,成傑就是這個班上的學生。我為這次暑期班講授的題目是“秦始皇東巡刻石及其文化意義”。成傑在課間上來與我交流,表示自己對石刻很有興趣,並表達了報考博士的意願。次年,他如願考上南京大學古典文獻學專業,從我攻讀博士學位。在我的博士弟子中,成傑屬於那種很早就明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人,他以“《金石萃編》與清代金石學”為博士論文選題,也比較早就確定了下來。從年到年,只有短短三年時間,除了要修畢學位課程、通過資格考試、完成一篇博士學位論文,還要發表規定的論文,大多數博士生都力不從心。對成傑來說,這卻不算太難的事,因為他極其用功,心無旁騖,將所有的時間精力都投入到讀書和寫作中。沒想到因為過於用功,臨畢業前累出病來,不得不住院休息了一段時間,但就是這樣,最終他也只用了三年零兩個月,就順利畢業了。
博士畢業不久,成傑就順利進入雲南大學歷史系博士後流動站,繼續從事金石學領域的專業研究。他利用天時地利,不辭辛勞,奔波於雲南各地,尋訪、蒐集了雲南各地的大量石刻文獻資料。他也抓緊時間,對博士論文補充材料,充實論述,擴大篇幅,提升水平。現在這本書終於要正式出版了,在跟廣大讀者見面之前,成傑請我說幾句。我作為這本書最早的讀者,也瞭解成傑寫作過程中的甘苦,姑贅以上數語,聊以為序。
年5月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