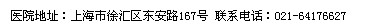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额窦炎 > 额窦炎诊断 > 回回药方的医学特色
回回药方的医学特色
回回医学在元明时代中国的应用,亦令其理论著作、方剂药书得到朝野人士的高度重视。元秘书监收藏的数以万计的伊斯兰各类科学书籍,其中就有“忒毕(医学)医经十三部”。与此同时,中国的回回医人为行医之便及传示门生、子弟之需,遂将这类回回医书译成汉文。这些医书的传人和译著抄本的传播,形成了对汉族固有的医药文化传统的新鲜与长期的刺激,对中国文化界认识、了解回回医学具有很大的帮助。为此,在具有远见卓识的、提倡科学文化事业的朝廷君主和政治家们直接推动下,由回回医人兼收并蓄了诸家回回医书的汉译抄本,分门类地编撰注释,历经数年,从后有了今日众所周知的《回回药方》。该书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见证,又是杰出的中国回回医学百科全书,更是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晶。《回回药方》是中国医学史上的瑰宝,是人们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史、医学史、本草学、医学、博物学、民俗学、东方哲学等多学科研究之无尽宝藏。
一、方药甚多
《回回药方》著者不明,现存红格明代抄本于北京图书馆善书部,成书年代为元代或元明之际。原书36卷,现仅存残本4卷。全书由汉文写成,但也混杂有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药物名、人物名、方剂名,尚有千余阿拉伯、波斯等地输入的药名、地名、人物名的汉字音译。现存4卷计页,约20万言。其中3卷载有方剂,其数量达首之多。内容兼有内、外、妇、儿、骨伤、皮肤、神经诸科及药物制剂、针灸等疗法。
《回回药方》以叙方为主,方论结合。残卷常用药物种,其中从阿拉伯中亚、西亚传人的香药多达种。其中就有诸多伊斯兰医学的传统用药,如东罗马的茴香(大茴香),喀布尔的诃梨勒,亚美尼亚的石头(天青石),印度的化食丹,犹太地面的膏子药,克尔曼的茴香,阿拉伯的橄榄油,索科特拉岛的芦荟,波斯的紫丁香及都龙知(吐根),东土耳其的龙胆、朵梯牙(皓矾)、可铁刺(西黄耆胶)、猩猩毛发、红宝石,还有亚美尼亚产的红玄武士,埃及产的缟玛瑙,尼罗河的柳果实以及松子仁、山香菜、西域芸香(漆树科乳香)、咱法兰(番红花)、阿飞勇(鸦片)、李子树胶(三额,阿拉伯树胶)、法尼的(碇子砂糖)、可落牙(产于亚美尼亚的茴香,维吾尔族称作“孜然”)、哈而八吉(藜芦)、海速木(洋蒿)、奄摩勒(余甘子)等。有些本是华化已久的胡药,如苏合香、荜拨、肉豆蔻、安息香、龙脑、胡椒、乳香、没药、腽肭脐、安石榴、血竭、阿月浑子、胡葱等。还有一些,如巴豆、肉桂、大黄、麻黄、黄连又是阿拉伯、西亚久用的产于中国的药物。
在药物剂型运用方面,《回回药方》大量地增加了丸、散、膏、酊剂的处方。这些方剂多以伊斯兰国家及穆斯林航海贸易所经诸热带国家出产的草本植物的汁液、乳汁(如墨牵牛子、芦荟)和木草植物的树脂胶汁(如乳香、安息香)。
二、滴鼻疗法
《回回药方》残卷中保存有阿拉伯芳香挥发药为主的露酒剂、糖浆剂、膏剂、漱口剂、药饼、搽药、贴药、渍药、取嚏剂及滴鼻剂等。尤其滴鼻剂的应用,颇令世人瞩目。书中收载滴鼻药剂方20多首,占总方剂数的4%。所治疾病不仅仅局限于鼻腔疾病,包括左瘫右痪、口眼歪斜、半身不遂、中风(缺血性脑血管病)、暗风(内风、高血压病)、尸强(暂时性脑缺血症、癔病)、衄血、耳痛、偏正头痛、头风(神经性头痛、额窦炎头痛)以及冷风头痛,适应范围相当广泛,且多用于治疗中风一类重危疾病,远非当今滴鼻剂仅囿于鼻部疾病治疗所能比拟。所使用的鼻药溶剂种类多样,如麦尔桑过失水、紫花油、撒答卜水、葡萄醴、骆驼尿、妇人乳汁、梅桂水、麻叶水等。鼻药的使用方式有滴、搐、吹、嗅,方剂有单方、复方、验方。药方组成少则一味(如纳尔丁油方),多则竟达一百多味(如马准西里撒方)。
除此之外,还有些药方除了修合制成丸、膏、散、汤供内服外,亦可随治疗需要调化合成滴鼻剂。诚然,通过鼻腔给药用以治疗疾病,并对用药途径和剂型以及适应证作如此详尽的阐述,这在中外医学史上实属少见,其学术成就、文献地位乃至现今开发利用,其价值都是不可低估的。
三、学术理论
《回回药方》中的医学理论体系,受阿拉伯伊斯兰哲学思想的影响,坚持“真一、阴阳、四元、三子”说,继承了中世纪医学理论的精华,即四体液、四性及禀性学说。四体液即白体液、红体液、黄体液、黑体液;四性,即冷(寒)、热、干(燥)、湿(润)。回回医学认为“四元”(土、火、水、气)为万有形色之宗元。四元不是四种“物质元素”,而是四种运动方式,这与其学术源渊的古希腊著名的“四元素”、古印度的“四大”及中医“五行”等有形物质结构说相去甚远。回回医学还将古希腊的“四质液”学说改造为(‘白、红、黄、黑”四液,并将其纳入元气、四性理论中加以运用。四元乃化生四体液的基础。每种“禀性”又是体液在人体中分布多寡及气质异常的表证,亦即每个人的禀性、气质又受体液的制约和调节。在“四性”中,其中相反的性质是不能共处于同一事物中,即有冷就无热,有燥则无润(湿)。冷只能与温或燥同在一物。所以,回回医学理论中特有的“四性”气质学说,实为与其他民族传统医学的主要区别。
阿拉伯伊斯兰医学承袭了古希腊的医学理论,将“四禀性”按其微显的不同程度,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等是最轻微的,第四等是最显著的。《回回药方》沿用其说,用以表述药物的詹眭和人体的病理变化。在表述病理过程中,又常提到“四根源”,如黑白根源、白疾根源,皆为体液性气质失常所致。
回回医学认为,机体“四性”的失调是疾病的根本,而“四性”的失调又常与“四体液”有关。疾病之根源,又多分为非体液性气质失调和体液性气质失调。体液性失调,即黑、白、红、黄四种体液(即根源)的异常变化。在论述疾病时,往往运用以原发病因加上气(禀性)因素,结合脏腑体液的异常程度的辨病与辩证相结合的方法,即“三维辩证法”。因此,回回医学在继承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运用伊斯兰哲学,能对自然生长的、存在的一切药物的属性,对人类体质特征、发病原因作出唯物的哲学解释,从而反映了《回回药方》成书时代,回回医学对疾病认识上是较成熟的,理论体系是较完备的。这些成就,既保存发扬了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的精华,同时也吸收融会了中国传统医学的部分内容,从而成为整理研究伊斯兰医学和现代医学的“另一半”,即被18世纪西方摒弃的体液及体质医学的珍贵资料。
四、正骨技术
《回回药方》的问世,促进了新的、与传统中医学风格迥异的完整医学体系的建立,包括新的理论、新的医术、新的卫生保健法。在《回回药方》残卷“折伤门”中,对骨伤的诊治最令人注目,给予中医体系颇大影响。如对骨折的愈合和治疗的论述:“凡人骨有损伤,小儿童子的可望再生。盖因初生的力还在其身内。若即壮年老人的,虽然辏接了,必无再生之力,却生一等物如脆骨,在其周回显出来。将损折处把定,如焊药一般。”这“焊药”一般的“脆骨”,即今日所称“骨痂”。儿童骨愈合速度比老年人提前1/2或2/3时间。又言:“接骨并移骨总治法,凡有二等:一等是扯,二等是栓系……对又折大者,用三条带栓,其栓是先放绢片,次用板。此等板宜用柔软木制者,如石榴木、柳木等的最可。又要光且匀。然此板当损折处栓欲牢固,非稍厚与硬不可用。”这种整复与固定并用夹板扎缚的技法,在中国是前无记载的。此法溯源于《希波克拉底文集》,被阿拉伯伊斯兰医学所采用、推广,后传人中国。所用治方,外敷为主,计有12方。内服仅4方,且多为内外兼治。对头部外伤的诊断,根据损伤组织划分,并分别使用不同的方法治疗。对外伤肿胀不忍且并发全身症状者,主张作“十”字切开,引流排脓。如论颅脑骨粉碎性骨折的碎骨片剔除法,改进脑手术及使用金属脓刀钻,《回回药方》中均作了详尽介绍,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使元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有了一大飞跃。随后李仲南《永类铃方》(年)、危亦林《世医得效方》(1年)中的正骨内容,与《回回药方》亦大致相同。故回回医学还以其精通各种手术而令中国人耳目一新,倍感神奇。回回医学对解剖学颇有研究,且无思想顾忌。残卷“折伤门”基本包括了古今骨科的软组织损伤、骨伤、关节脱臼及其合并症,并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些损伤的原因、发生机理、诊断和治法,从而反映了元代中国骨伤诊疗水平及发展成就。
五、烙灸疗法
《回回药方》卷三十四,“针灸门”专论三大灸法(艾灸、药灸、烙灸)。其中“烙灸”源于中世纪阿拉伯最杰出的医学家卡赛姆(~lOl3年)。在其所著的《方法》一书中特别论述烧灼(烙灸)并作了详尽的描述,故回族医人对烙灸非常重视。烙灸法,适应证分为16种,可治疗内科、外科、伤科、眼科、皮肤科等多种疾病。其病因多与体内“恶润”有关。具体方法是,采用多种器械烙灼皮肤及相应穴位,令其破损、溃烂、流脓,促使体内“恶润”排出,然后用生肌收回药,使之平复。
目前,《回回药方》已引起中外学者的特别北京白癜风治疗最好医院电话白癜风怎么治疗最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