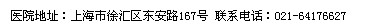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额窦炎 > 额窦炎饮食 > 陈望衡史前中华民族的人天关系观上古
陈望衡史前中华民族的人天关系观上古
北京看白癜风哪家医院最权威 http://baidianfeng.39.net/bdfby/yqyy/摘要
人天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我们可以从神话传说与考古文物两个角度来认识史前中华民族的人天关系观:(1)人天一体,体现为盘古开天地神话。(2)人代天工,体现为女娲补天神话。(3)神为超人,体现为史前的神像雕塑。(4)中介通天,体现在玉为神物,以玉通天。(5)人天分职,体现为颛顼“绝地天通”传说。史前初民关于人天关系的诸多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人天关系观提供了精神资源。
关键词史前神话人天关系
人天关系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天在中国哲学中有自然、自然规律、神灵三个方面的涵义。中华民族人天关系观在先秦基本上已经建立,后来只是丰富与发展,然而如果溯其源头,则可达史前。史前没有文字,但不等于史前初民没有观念,史前初民的人天观念通过他们制作的物件体现出来。另外,有关远古的神话与传说虽然作为文字产生较晚,但仍然可以作为了解史前初民生活情况的参考。从这些神话与传说中,我们可以了解初民们关于人天关系的一些基本观念。
一、盘古开天地——人天一体
中国史前有关宇宙创造的神话,最重要的是盘古的故事。这个故事有几个版本,大同而小异,《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记》云: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1]
这里,有一个要点值得注意,盘古在天地中,天地变,他也变。天变大,他就变大,天变高,他就变高。这就是说,盘古并不外在于天地,而且也没有明确说是天地生盘古,只是说“盘古生其中”,这“生其中”指生于其中。
在《五运历年纪》中,盘古与天地的关系就不同了:
元气濛鸿,萌芽兹始,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2]
比较上述两说,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宇宙开始于濛鸿或者说混沌。这个观点中国其他古书也是接受的。《淮南子》还具体说到混沌是什么样子:“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窈窈冥冥,芒芠漠闵;澒蒙鸿洞,莫知其门。”[3]这种描述我们在《老子》一书中也看到,老子用它来描述“道”,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4]。可见道就是未分时的天地。《周易》说这就是“太极”。太极、道作为宇宙的本体,它是整一的,无限的,无形的,不可把捉的(因为一把捉它就成为有限的了),但又是实际存在的。中国人的哲学一元观就从这开始。
第二,宇宙始分为阴阳,阴阳具体化为乾坤,乾为天,坤为地。天上长,地下降。《三五历记》还确定了阴阳的基本性质:阳为清,阴为浊。不管从语言表达方式上,还是思想实质上,盘古生天地的逻辑颇似《周易·系辞上传》中所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5]
《绎史》引《五运历年记》关于盘古的故事与《艺文类聚》引《三五历记》中关于盘古的故事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三五历记》中的盘古虽随着天地扩大而扩大,但自己不参与天地的创造;而《五运历年记》中的盘古,却以自己的身体参与天地的创造,具体来说,盘古死后,其身体的各部分相应地化成为天地万物,包括让身上的小虫化为黎民百姓。
这一故事隐含着这样一个观点:盘古与天地是一体的。一方面,天地生盘古,而且还是天地的第一生物(首生盘古),说明天地是盘古之祖;另一方面,盘古将自己的血肉化为天地中的万物,这可以说盘古生天地,盘古倒成了“天地万物之祖”。这种互生,说明盘古与天地存在着血缘性的关系。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思想“天人合一”可以溯源到此,具体来说,有这样几个要点:
(一)中华民族的哲学其实是分客体与主体的,天地是客体,盘古是主体。主体是由客体决定的,正如盘古是天地生的,而且是“首生”的。
(二)中华民族的哲学中的客体与主体其实也是可以互生的。一方面,天地自然生盘古,另一方面,盘古也可以将自己身上的东西转化为天地自然。
(三)中华民族的哲学更为看重人的主体性。虽然中华民族的哲学给了天地即客体以本体的地位,承认天地生万物,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的哲学也强调人参与宇宙的创造,故而在实际效果上,凸现出的是人的作用、人的精神、人的智慧。上引《五运历年纪》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虽然故事开头也说到了天地“首生盘古”,但它突出的是盘古如何创造天地。
(四)中华民族的哲学在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中突出的是精神的力量。盘古开天地不仅有身体的参与,还有情感的参与。《述异记》中说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中有这样几句话:“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又说“盘古泣为江河”[6],所以,盘古开天地,不只是有身体的对象化,还有情感的对象化。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期后,不论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哲学,均将精神的力量发扬到极致。
(五)中华民族哲学看重天人对应性。盘古开天地的神话中,盘古将自己的身体转化成相应的自然物,比如,他将气化为风云,声化为雷霆,血液化为江河,左眼化为太阳,右眼化为月亮,等等。这种对应性的转化,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类比思维。类比思维是人类共同的思维方式,不独中华民族有,但中华民族将类比思维发展到极致的地步。
归纳以上五点,可以概括为“天人合一”思想。一般来说,天人合一思想不只是中华民族有,其他民族也有,但各有自己的特点。从盘古开天地故事所导出的人天关系观,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人天关系观的某些特点,比如,人天的互生性、对应性、精神性以及人在人天关系中的主体性、能动性等。中华民族“天人合一”思想,最大的缺点是没有充分地导向实践,基本上只停留在精神领域,因而未能以这种思想去促进科学技术及生产实践的发展。
二、女娲补天——人工代天
盘古开辟的天地本来有序地运转着,但共工氏与颛顼氏争帝的一场战争将这种秩序打破了。惨遭失败的共工大怒,触不周之山,致使“天柱折,地维绝”。在这种严峻的情势下,一位拯救世界的女神出来了,她就是女娲氏。《淮南子·览冥训》详尽地记载了女娲氏补天救世的英勇行为: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彩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7]
这一故事中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
第一,炼五彩石以补苍天。女娲不是炼普通石头而是炼五彩石来补天,首先说明史前先民对天空之美有着强烈的感受。其次,能将石头炼成汁液来补天,说明当时的冶炼技术已经达到很高水平。这种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早在距今一万年以前人们就会制陶了。既然陶泥能烧,石头也就能烧。
第二,盘古是将自己的身体化为天地万物的,而女娲是炼五彩石补天的。人体化物,纯粹是想象,不含科学成分;而以物化物,虽然也有想象,却含有一定的科学成分。由人体化物到以物化物,明显见出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在提高。女娲时代进步于盘古时代。
女娲终于做完了她要做的事,然后死了,她的死同样有助于世。《山海经·大荒西经》云:“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8]女娲静静地躺在她修补好的大地上,那是一片广漠的土地,遍长着森林。她死了,犹如当年盘古的死,肉体化成了天地万物。与盘古不同的是,女娲不仅用她的肉体,化出了河流、树林、云霞等等,还让她的肠子化出十位神人。这用肠化成神,即是说用人体化成了神体。神人一体。这一说法暗含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神是人的产物,准确地说是人的精神的产物。《山海经》不能精当地说神是人的精神的产物,而说是肠的产物。
女娲补天与盘古开天地,所体现出来的基本意义是一致的,但女娲补天的意义似在盘古开天地意义的基础上有所延伸、拓展。
(一)物质与生命的关系:盘古与女娲都造了天地万物,细比较一下他们造的物,盘古造的物仅为物,一件件的物,文献资料中没有说这些物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具有生命的意味,然而,女娲造的,不是一件件的物,还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上面所引《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到女娲补过的天,不仅恢复了它的完整,而且恢复了它的生命,“和春阳夏,杀秋约冬”[9]。春夏秋冬的运转都不是物质性的,而是生命性的,所以有“和”,有“阳”,有“杀”,有“约”。宋代大画家郭熙说:“真山水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静而如妆,冬山渗淡而如睡。”[10]此说与上说可谓一脉相承。
(二)人工与天工的关系:这个故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女娲补天用的材料。女娲是从大地取材补天的,这说明地与天具有同一属性,不然怎么能用地补天呢?中华民族传统的哲学观念中,天地既相对,又相通,还相成。女娲用地面上的材料补天就是一个证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女娲不是直接地用地上的材料补天的,取自于地上的五彩石须经过人工烧化成汁液才能补天。这一点十分重要,它说明,地与天虽然相通或相成,但地材化成天须经过人工这一中介。这一思想直接导致《周易》中“三材”说的产生。“三材”为天、人、地。三者共同构造了宇宙,缺一不可。
(三)人心与天心的关系:盘古之开天辟地,女娲之补天救世,一切匪夷所思,却又顺情顺理,合人心,合民意。《淮南子·览冥训》叙述女娲补天后,天地秩序井然:
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背方州,抱圆天;和春阳夏,杀秋约冬,枕方寝绳;阴阳之所壅沉不通者,窍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当此之时,卧倨倨,兴眄眄;一自以为马,一自以为牛;其行蹎蹎,其视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魉不知所往。当此之时,禽兽蝮(虫)蛇,无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无有攫噬之心。[11]
百姓们一如牛马,自由自在,天地万物“皆得其和”,而女娲则乘雷车,驾应龙,悄然而去,“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12]。如果说天有心,则此心同于人心,中华民族哲学的最高概念———道,既是天心又是人心。宋代理学家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天心本就是人心。
三、神为人像——以人拟天
史前初民对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神的理解,所以,人天关系往往演绎为人神关系。
在人类的心理中,神有三类:一类是至高神,天帝、上帝等;一类为祖先神,即逝去的祖先、部落首领、英雄等;第三类为自然神灵,如日神、月神、山神、水神、雷神、动植物神灵等。
三类神灵,最切近人的应是祖先神。祖先神原本是人,死后化为神,因此,他们不仅具有人的思想情感,而且还具有人的形象。自然神灵的形象,一般兼有自然因素,但主体是人。至于至高神,在中国古代宗教中,都是人的形象。
先民们对神灵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要从人自身出发,将神想象成善神与恶神,善神集中着人世间能有的一切善,而且将其无限地放大;同样,恶神则集中着人世间能有的一切恶,而且将其极度地夸张。神性就这样成为放大了的人性。人的一切优点神全有,人的一切缺点神也全有。神可能是最好的人,也可能是最坏的人。从本质上看神即为超人。
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人物雕塑,有泥塑,有陶制,也有玉制。这些人物雕塑或是单独存在,或是与器物造型结合在一起。一般来说,单独存在的人物雕塑应是作为神人而存在的,在祭祀活动中他就代表神,是人们祭祀的对象。辽宁丹东东沟兴隆洼文化遗址出土三件滑石人头像,是距今年前初民的作品。这种单独的人物造像,在史前多有发现,大体上均可以认定为神。新石器晚期肖家屋脊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制人头像(图1),面目狰狞,形象冷酷,透出与人的一种隔膜感,更是可以认定为神了。
图1
与器物造型相结合的神像一般只作为神物而存在,也就是说,它并不代表神,只是表示此物具有神性,或体现有神意。大地湾出土的一件陶罐,其口部与颈部给塑造成人头,这件陶罐不应是一般的用品,而是一件神物。
人物雕塑,不论是作为单独造型,还是结合器物造型,均有整体造型与局部造型两种,整体造型一般来说突出的是头部,而局部造型也多取头部。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内蒙古阴山、宁夏贺兰山、福建华安仙人潭以及台湾万山岩等地的远古岩画中,好些神像只有头部(图2)。原始初民已经意识到人的头部是智慧的源头,而且在人体中它具有最大的魅力。在以人像替代神像的时候,无疑应该突出头部。
图2
原始初民是不是隐约地感受到精神的力量?神的本质是精神。精神是看不到的,神应该也是看不到的。但是,神如果不显现为具体的形象,人们难以接受。既要让神显现,又不要让人误解神是具体的人,就只有突出神的头部,虚化或弱化神的身体了。
以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形象,将对人的审美心理移置并提升为对神的审美心理,这是中华民族审美意识的一个突出特征。这一审美意识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红山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发现,莫过于牛河梁遗址中的女神像(图3)。
图3
参与此次发掘的考古学家郭大顺如此生动而详尽地描绘这尊女神出土的情景以及女神头像的细部:
……头像存高22.5厘米,正好相当于真人原大。为高浮雕式……唇部涂朱,为方圆形扁脸,颧骨突起,眼斜立,鼻梁低而短,圆鼻头,上唇长而薄,这些都具有蒙古人种特征。头像额部隆起,额面陡直,耳较小而纤细,面部表面圆润,面颊丰满,下颌尖圆,又深富女性特征。[13]
这尊女神像被置入面积极为窄小的女神庙中,为高浮雕,背部紧贴后墙。这样的女神庙是不能让很多人同时进入的。这样做,史前初民肯定是有所考虑的,也许为的是突显女神的神秘性,由神秘导出崇高;也许它就只容许主祭者(部落最高首领)进入,体现祭祀权的专一。祭祀权是部落权威之一,甚至它还可能是部落权威的最高体现。
这女神究为何神?学界有不同说法。考古学家苏秉琦说:“女神是由年前的‘红山人’模拟真人塑造的神像(或女祖像),而不是由后人想象创造的‘神’,‘她’是红山人的女祖,也是中华民族的‘共祖’。”[14]这一说法看来更能为人们所接受。
中华民族对祖先神的情感来自对祖先的情感,这种情感有什么特点呢?首先是血缘性的依恋感。其次是视为超人的敬畏感。祖先既然是神,它就具有常人不可能具有的本领,能克服常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因此,祖先神在初民的心目中地位超过了英雄,它不仅是人们敬畏的对象,而且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中华民族对于神的这种情感后来泛化为对天地自然的情感。将天地自然看做是人的祖先,看做是人的母体,于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就成为人内心的需求。为什么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说、“道法自然”说具有浓郁的血缘意味和情感色彩,究其源头,还在于中华民族先民心目中的神,其代表性形象是祖先。
从史前神像的雕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史前初民是以人拟神的,由于神在初民的心目中即为天,所以,这一思维也可以理解成以人拟天。这以人拟天实质是以天为祖,以祖拟天。
四、玉为神物——以玉通天
史前巫风昌炽,几乎所有的活动都有不同程度的巫术存在。巫术的目的是与神即与天沟通,沟通不能是直接的,需要借助物,这物当然要贵重,要精美。无疑,在史前,最贵重、最精美的器物莫过于玉器了。因此,史前的玉器充当了通神的重要中介,它们不是一般的物,而是神物。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第十三》中有一段风胡子与晋郑王关于兵器的对话。风胡子说:“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15]为什么说玉为神物?玉与神有什么样的关系?按《山海经》的说法,黄帝喜欢吃玉,不仅黄帝喜欢吃,“天地鬼神,是食是飨”[16]。正因为玉是神灵喜欢的食物,产玉的地方就成为神仙的家。昆仑山产玉,而昆仑山“实惟帝之下都”[17]。这样的玉山,不只昆仑一座。不仅神仙喜欢居住在产玉的地方,而且凡产玉的地方,也多出神异之物。玉与神、灵物、怪兽、奇禽结下不解之缘。玉既然能如此获得神灵的欢心,玉器就成为献给神的最好礼物。
史前,玉器成为初民通神最为重要的中介。为了更好地实现玉器通神的功能,玉器是需要精心制作的,一般来说,主要是制成两种形式:
第一,将玉器做成神物,这神物又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做成普通的动物,如红山文化中的玉蝉、玉鴞,石家河文化中的玉虎头,这些动物在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但是,因为它们具有的特殊本领为人所仰慕,于是为之塑像,当做物神,寄寓着人们美好的希望。二是做成奇异的动物,如红山文化中的玉猪龙、C形龙(图4),凌家滩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的盘龙,还有石家河文化中的玉凤(图5)。这些动物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是诸多动物元素拼合的产物,是更高的动物神灵形象,寄托着初民们更高的理想与愿望。
图4
图5
第二,将玉器做成巫师形象,这巫师有比较写实的,如凌家滩的玉人(图6),也有戴着面具或画了脸谱的,如石家河的玉人首佩。年在高淳朝墩头出土一套玉挂饰,属于良渚文化。“挂饰由17件饰件构成,顶部为一立人形,头大身小,似有宽大的发髻,枣核形眼眶,宽鼻,阔口,似穿方领长衫,袖手。”[18]此玉人形象虽然简约,但已有发式、衣着等,是迄今所见良渚文化人形玉器较完整的、写实的造型。
图6
第三,玉琢法器。古代巫觋通神,通常需要借助于祭祀、歌舞这样的仪式,在这些原始的宗教仪式中,巫师手中通常要摆弄一些特殊的器具,这些器具有一些是用玉制作的。凡用来作为通神工具的器物我们统称为“法器”。现在学者们都认为,良渚出土的琮是重要的法器,玉琮上面雕刻有神人兽面的神徽图案(图7)。
图7
几乎所有的史前人类在实施与天沟通时都要借助于一定的器物,也就是说,通天需要中介,但各民族所用的中介是不一样的。中华民族独重玉器,将它看做通天的最重要器物,而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玉的功能发生变化,由通天的中介成为君子的象征,由此发展出具有独特内涵的玉文化,这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虽然玉在文明时代主要是以君子的象征而体现它的价值,但是它的通天功能只是淡化、消隐,而没有消失。将两项功能联系起来,无异于表示唯君子才能通天,这天当理解为天志、天理。
五、“绝地天通”——人神分职
关于人天沟通问题,《国语·楚语》有五帝之一颛顼“绝地天通”的记载:
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19]
这段文章为观射父回答楚昭王提问的一部分,讨论的是人与神沟通的问题,按观射父的看法,古时,民和神不相混杂。人民中,只有极少数人能通神,这人男的叫觋,女的叫巫。巫与觋在品德上均有很高的要求,他们的工作很明确,也做得很到位。于是,神灵降福,财用不匮,天下太平。然而到黄帝儿子少皞氏即金天氏的时代,这良好的法度衰落了。九黎族乱德,民神杂糅,人人自作祭祀,家家自为觋巫。民无诚信,祭祀无法,严重亵渎了神灵。结果,谷物歉收,灾祸频仍,生机丧尽。颛顼继位做了国君后,命令南正重这位大臣专管与天上神灵沟通的工作,火正黎这位大臣专管地面百姓的工作。天与地、神与民各不相扰,不相侵渎,这叫作“绝地天通”。
“绝地天通”意义是巨大的:第一,它端正了天与地(人类社会)的关系,天有天则,地(人类社会)有地规。二者虽相应但不相扰。第二,它端正了神民的关系,神有神的序列,民有民的序列。序列中包含有尊卑之别、高下之别,不可混淆。第三,它严肃了祭祀制度,重树了神的威严。第四,它严肃了政权的职责,重树了政府的威严。
“绝地天通”对中华民族以后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民族不否定天国的存在,也不否定神灵的存在,但是,不让天国、神灵侵扰人类正常的生活。天地神灵是要祭的,但祭天地神灵有一套专门程序,不可淆乱,而且须由有一定资质的专人来做,有关祭祀的礼仪制度在《周礼》《仪礼》《礼记》中有明细的记载。
于是,神灵的秩序建立起来了,社会的秩序也建立起来了。考察中华民族的文化,我们发现它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它一方面讲天人合一,讲神人合一;另一方面又讲天人两分,神人两隔。讲前者,是让人们亲和天,亲和神,从感情上接受天,接受神;讲后者,则强调天对人、神对人的尊严性、权威性,让人恐惧天,恐惧神,从而自觉地服从天,服从神。这两个方面既相对,又相补;既相应,又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生态体系。
注释
[1][2][6]袁珂、周明编:《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版,第6、7、7页。
[3][7][9][11][12]杨坚点校:《吕氏春秋·淮南子》,岳麓书社年版,第68、64、65、65、65页。
[4]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年版,第页。
[5]朱熹注:《周易》,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8][16][17]《山海经校译》,袁珂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29、30页。
[10]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年版,第13页。
[13][14]郭大顺:《红山文化考古记》,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第62~63、66页。
[15]李步嘉校释:《越绝书校释》,武汉大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18]尤仁德:《古代玉器通论》,紫禁城出版社年版,第27页。
[19]邬国义等:《国语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第~页。
原文刊发于《江海学刊》年第02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史前审美意识研究”(项目号:09BZX)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望衡(—):男,湖南邵阳人。日本大阪大学文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景观文化研究规划中心主任、湖北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学学会理事、国际应用美学研究学会国际理事会副主席。研究方向:中国美学史、环境美学,代表作:《中国古典美学史》、《当代美学原理》、《环境美学》等。
北京师范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邹芒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