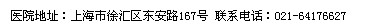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额窦炎 > 额窦炎饮食 > 黄帝外经上篇
黄帝外经上篇
白癜风治疗医院 http://m.39.net/pf/bdfyy/
关于《黃帝外經》
一、《黃帝外經》首見於《漢書》卷三十,藝文志第五,方技類之醫經中,惟不見錄經文。相關之書目為:黃帝外經三十九卷或三十七卷。另有扁鵲外經十二卷。又有白氏外經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等。
二、據梅自強先生《顛倒之術》謂:「此書(黃帝外經)一直失傳,至本世紀八十年初,始在天津發現明末或清初根據口耳相傳整理而成的精抄本。」傳述者(陳士鐸先生远公)於每篇之末都加上了簡短的評價,並冠以《外經微言》之名。爾後,天津古籍出版社曾把它列為「中醫珍本叢書」影印本試銷,不意以不是岐伯時成書為由而被某些人說成是「偽書」,以致未能再版。」
又謂:「《外經》是以黃帝及雷公、風伯等二十三位大臣探討問難的方式寫成的,共九章八十一篇。《外經》的內容,有不少是可補《內經》之不足。(按:即仙道內丹、養生延命範圍)」
《外经微言》概述
《外经微言》是年整理古医籍过程中发现的,该书现藏于天津市卫生职工医学院图书馆。本书前无序,后无跋,封皮残缺,印章亦已模糊难辨。卷首有“岐伯天师传,山阴陈士铎号远公又号朱华子述”字样,其书末朱题“嘉庆二十年静乐堂书”,其笔体与正文稍异,疑或后人所加。经有关专家鉴定为清代精抄本。经查阅多种图书目录,均未见记载《外经微言》一书,后查《山阴县志》方知陈士铎确有此书行世。
嘉庆八年《山阴县志》:“陈士铎,邑诸生,治病多奇中,医药不受人谢,年八十余卒,所著有《内经素问尚论》、《灵枢新编》、《外经微言》、《本革新编》、《脏腑精鉴》、《脉诀阐微》、《石室秘录》、《辨证录》、《辨证玉函》、《六气新编》、《外科洞天奥旨》、《伤寒四条辨》、《婴孺证治》、《伤风指迷》、《历代医史》、《济世新方》、《琼笈秘录》、《黄庭经注》、《梅花易数》等书行世。”
《外经微言》全书九卷,每卷九篇,共八十一篇专题论述。其中第一卷论述养生、天癸、月经、子嗣、寿夭等;第二卷论述经络终始、标本顺逆;第三、四、五卷论述五行生可、脏腑气化;第六、七卷论述五运六气、四时八风;第八卷论述伤寒、瘟疫;第九卷论述阴阳寒热等。
《外经微言》丰富多彩,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医理论性著作。其理论基础主要本于《内经》,现将其主要学术思想简介如下:
一、《外经微言》中有很多养生的论述,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如《顺逆探原篇》提出了“逆而顺之必先顺而逆之,绝欲而毋为邪所侵也,守神而毋为境所移也,练气而毋为物所诱也,保精而毋为妖所耗也。服药饵以生其滓,慎吐纳以添其液,慎劳逸以安其髓,节饮食以益其气”的养生方法。在《命根养生篇》篇末附“陈远公曰:精出于水,亦出于水中之火也。精动,由于火动;火不动,则精安能摇乎。可见精动由于心动也,心动之极则水火俱动矣。故安心为利精之法也。”着重指出了“精”在人身的重要意义,并申明了“安心”为养精的重要方法。《善养篇》论述了调节阴阳平衡的重要性,并介绍了养阴养阳的方法。综上所述,可知《外经微言》中主要从安心、守神、保精等方面较全面地阐述了养生之道,与《内经》中有关养生的经义可谓相得益彰。
二、《外经微言》中有《肺金篇》、《肝木篇》、《肾水篇》、《心火篇》、《脾土篇》、《胃土篇》等十三篇专门论述五脏六腑的生克关系和宜忌常变的原理,以及脏腑病变的治疗原则,对内经五行生克学说有所发展。兹以《肺金篇》为例介绍如下,其云:“少师问曰:肺金也,脾胃土也,土宜生金,有时不能生金者谓何?岐伯曰:脾胃土旺而肺金强,脾胃土衰而肺金弱,又何疑乎。然而脾胃之气太旺,反非肺金所喜者,由于土中火气之过盛也。”简明地论述了脾土和肺金的关系。《肺金篇》又云:“土为肺金之母,火为肺金之贼。肺近火,则金气之柔者必销矣。然肺离火,则金气之顽者必折矣。所贵微火以通薰肺也。故土中无火,不能生肺金之气。而土中多火,亦不能生肺金之气也。所以烈火为肺之所畏,微火为肺之所喜。……”进而申明肺金喜土中微火之温煦,而恶烈火之熏灼。《肺金篇》扼要地说明了肺金和肝木在正常、反常两种情况下的相互关系,阐述了肺位居上,易受火刑的道理。并指出:“肺为娇藏,曷禁诸火之威逼乎。金破不鸣,断难免矣。何以自免于祸乎?岐伯曰:仍赖肾子之水,以救之。是以肺肾相亲,更倍于土金之相爱。以土生金,而金难生土。肺生肾,而肾能生肺,昼夜之间,肺肾之气实,彼此往来两相通,而两相益也。……少师曰:善。请问金化为水,而水不生木者,又何谓乎?岐伯曰:水不生木,岂金反生木乎。水不生木者,金受火融之水也。真水生木而融化之,水克木矣。”阐述了肺受火刑而致金破不鸣的治疗原则,从而明确了肺与肾的密切关系,并进一步说明了水生木和水克木的道理。可以看出,陈士铎不仅是一个造诣很深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临床家,因为他能灵活地运用五行学说和脏腑气化学说,将《内经》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的辨证法则融为一炉,从而阐发了《内经》的有关理论。
三、《外经微言》对《内经》的经络学说及六气学说等论述都有所阐发。《外经微言?考订经脉篇》云:“雷公曰:脾经若何?岐伯曰:脾乃土藏,其性湿……其脉起于足之大指端,故又曰足太阴也。脾脉既起于足下,下必升上,由足大指内侧肉际,过横骨后,上内踝前廉,上踹内,循胫骨后,交出厥阴之前,乃入肝经之路也。夫肝木克脾,宜为脾之所畏,何故脉反通于肝,不知肝虽克土,而木亦能成土,土无木气之通,则土少发生之气,所以畏肝,而又未尝不喜肝也。……脾与胃为表里,脾内而胃外,脾为胃所包,故络于胃。脾得胃气,则脾之气始能上升,故脉亦随之上鬲,趋喉咙而至舌本,以舌本为心之苗,而脾为心之子,子母之气自相通而不隔也。然而舌为心之外窍,非心之内廷也,脾之脉虽至于舌,而终未至于心。故其支又行,借胃之气,从胃中中脘之外上鬲,而脉通于膻中之分,上交于手少阴心经,子亲母之象也。”以上论述则是在《灵枢?经脉篇》的基础上,用脏腑经络气化学说进一步阐述经脉循行络属的原理。
据《辨证录?凡例》:“岐天师传书甚富,而《外经》一篇尤奇,篇中秘奥,皆采之《外经》,精鉴居多,非无本之学也。铎晚年尚欲笺释《外经》,以求正于大雅君子也。”由此可知《外经微言》是陈士铎晚年在医学理论上集大成的著作,其中八十一篇专题论述,每篇各有特色,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内经》的理论,是学习和研究中医学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黄帝外经》上篇
陰陽顛倒篇第一
黃帝聞廣成子窈窈冥冥之旨,歎廣成子之謂天矣。退而夜思,尚有未獲。遣鬼臾區問于岐伯天師曰:帝問至道于廣成子。
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無思慮營營,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汝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身可以不老也。天師必知厥義,幸明晰之。
岐伯稽首奏曰:大哉言乎,非吾聖帝安克聞至道哉。帝明知故問,豈欲傳旨于萬祀乎,何心之仁也!臣愚,何足知之。然仁聖明問,敢備述以聞。窈冥者,陰陽之謂也。昏默者,內外之詞也。視聽者,耳目之語也。至道無形而有形,有形而實無形。無形藏於有形之中,有形化於無形之內,始能形與神全,精與神合乎。
鬼臾區曰:諾,雖然,師言微矣,未及其妙也。
岐伯曰:乾坤之道,不外男女。男女之道,不外陰陽。陰陽之道,不外順逆。順則生,逆則死也。陰陽之原,即顛倒之術也。世人皆順生,不知順之有死;皆逆死,不知逆之有生,故未老先衰矣。
廣成子之教示帝行顛倒之術也。
鬼臾區贊曰:何言之神乎。雖然,請示其原。
岐伯曰:顛倒之術,即探陰陽之原乎。窈冥之中有神也,昏默之中有神也,視聽之中有神也。探其原而守神,精不搖矣。探其原而保精,神不馳矣。精固神全,形安能敝乎。
鬼臾區覆奏帝前。
帝曰:俞哉,載之《外經》,傳示臣工,使共聞至道,同游於無極之野也。
陳士鐸曰:此篇帝問而天師答之,乃首篇之論也。問不止黃帝,而答止天師者,帝引天師之論也。帝非不知陰陽顛倒之術,明知故問,亦欲盡人皆知廣成子之教也。
順逆探原篇第二
伯高太師問于岐伯曰:天師言顛倒之術,即探陰陽之原也,其旨奈何?
岐伯不答,再問曰,唯唯三問。
岐伯歎曰:吾不敢隱矣。夫陰陽之原者,即生克之道也。顛倒之術者,即順逆之理也。知顛倒之術,即可知陰陽之原矣。
伯高曰:陰陽不同也。天之陰陽,地之陰陽,人身之陰陽,男女之陰陽,何以探之哉?
岐伯曰:知其原亦何異哉!
伯高曰:請顯言其原。
岐伯曰:五行順生不生,逆死不死。生而不生者,金生水而克水,水生木而克木,木生火而克火,火生土而克土,土生金而克金,此害生於恩也。死而不死者,金克木而生木,木克土而生土,土克水而生水,水克火而生火,火克金而生金,此仁生於義也。夫五行之順相生而相克,五行之逆不克而不生。逆之至者,順之至也。
伯高曰:美哉言乎。然何以逆而順之也?
岐伯曰:五行之順,得土而化。五行之逆,得土而神。土以合之,土以成之也。
伯高曰:餘知之矣。陰中有陽,殺之內以求生乎。陽中有陰,生之內以出死乎。余與帝同遊幹無極之野也。
岐伯曰:逆而順之,必先順而逆之。絕欲而毋為邪所侵也,守神而毋為境所移也,練氣而毋為物所誘也,保精而毋為妖所耗也。服藥餌以生其津,慎吐納以添其液,慎勞逸以安其髓,節飲食以益其氣,其庶幾乎。
伯高曰:天師教我以原者全矣。
岐伯曰:未也,心死則身生,死心之道,即逆之之功也。心過死則身亦不生,生心之道又順之之功也。順而不順,始成逆而不逆乎。
伯高曰:志之矣,敢志秘誨哉。
陳士鐸曰;伯高之問,亦有為之問也。順中求逆,逆處求順,亦死克之門也。今奈何求生於順乎。于順處求生,不若于逆處求生之為得也。
回天生育篇第三
雷公問曰:人生子嗣,天命也。豈盡非人事乎?
岐伯曰:天命居半,人事居半也。
雷公曰:天可回乎?
岐伯曰:天不可回,人事則可盡也。
雷公曰:請言人事。
岐伯曰:男子不能生子者,病有九;女子不能生子者,病有十也。
雷公曰:請晰言之。
岐伯曰:男子九病者:精寒也,精薄也,氣餒也,痰盛也,精澀也,相火過旺也,精不能射也,氣鬱也,天厭也。女子十病者:胞胎寒也,脾胃冷也,帶脈急也,肝氣鬱也,痰氣盛也,相火旺也,腎水衰也,任督病也,膀胱氣化不行也,氣血虛而不能攝也。
雷公曰:然則治之奈何?
岐伯曰:精寒者,溫其火乎。精薄者,益其髓乎。氣餒者,壯其氣乎。痰盛者,消其涎乎。精澀者,順其水乎。火旺者,補其精乎。精不能射者,助其氣乎。氣鬱者,舒其氣乎。天厭者,增其勢乎,則男子無子而可以有子矣。不可徒益其相火也。胞胎冷者,溫其胞胎乎。脾胃冷者,暖其脾胃乎。帶脈急者,緩其帶脈乎。肝氣鬱者,開其肝氣乎。痰氣盛者,消其痰氣乎,相火旺者,平其相火乎。腎水衰者,滋其腎水乎。任督病者,理其任督乎。膀胱氣化不行者,助其腎氣以益膀胱乎。氣血不能攝胎者,益其氣血以攝胎乎,則女子無子而可以有子矣。不可徒治其胞胎也。
雷公曰:天師之言,真回天之法也。然用天師法男女仍不生子奈何?
岐伯曰:必夫婦德行交虧也。修德以宜男,豈虛語哉。
陳士鐸曰:男無子有九,女無子有十,似乎女多於男也。誰知男女皆一乎,知不一而一者,大約健其脾胃為主,脾胃健而腎亦健矣,何必分男女哉。
天人壽夭篇第四
伯高太師問岐伯曰:余聞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堅脆,皮有厚薄,可分壽天然乎?
岐伯曰:人有形則有氣,有氣則有骨,有骨則有肉,有肉則有皮。形必與氣相合也,皮必與肉相稱也,氣血經絡必與形相配也,形充而皮膚緩者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天。形充而脈堅大者,氣血之順也,順則壽。形充而脈小弱者,氣血之衰也,衰則危。形充而顴不起者,肉勝於骨也,骨大則壽,骨小則天。形充而大,肉(月囷)堅有分理者,皮勝於肉也,肉疏則天,肉堅則壽。形充而大肉無分理者,皮僅包乎肉也,肉厚壽,肉脆夭。此天生,人不可強也,故見則定人壽夭,即可測人生死矣。
少師問曰:誠若師言,人之壽天天定之矣,無豫於人乎?
岐伯曰:壽夭定於天,挽回天命者人也。壽夭聽於天;戕賊其形骸,瀉泄其精髓,耗散其氣血,不必至天數而先天者,天不任咎也。
少師曰:天可回乎?
岐伯曰:天不可回,而天可節也。節天之有餘,補人之不足,不亦善全其天命乎。
伯高太師聞之曰:岐天師真善言天也。世人賊夭之不足,烏能留人之有餘哉。
少師曰:伯高非知在人之天者乎。在天之夭,難回也。在人之夭,易延也。吾亦修吾之天,以全天命乎。
陳遠公曰:天之天難延,人之天易延。亦訓世延人之夭也。伯高之論,因天師之教而推廣之,不可輕天師而重伯高也。
命根養生篇第五
伯高太師複問岐伯曰:養生之道,可得聞乎?
岐伯曰:愚何足以知之。
伯高再問。
岐伯曰:人生天地之中,不能與天地並久者,不體天地之道也。天錫人以長生之命,地錫人以長生之根。天地錫人以命根者,父母子之也。合父母之精,以生人之身,則精即人之命根也。魂魄藏於精之中,魂屬陽,魄屬陰,魂趨生,魄趨死。夫魂魄皆神也。凡人皆有神,記憶體則生,外遊則死。魂最善遊,由於心之不寂也。
廣成子謂:抱神以靜者,正抱心而同寂也。
伯高曰:夫精者,非腎中之水乎?水性主動,心之不寂者,不由於腎之不靜乎?
岐伯曰:腎水之中,有真火在焉。水欲下而火欲升,此精之所以不靜也。精一動而心搖搖矣。然而制精之不動,仍在心之寂也。
伯高曰:吾心寂矣,腎之精欲動奈何?
岐伯曰:水火原相須也,無火則水不安,無水則火亦不安。制心而精動者,由於腎水之涸也。補先天之水以濟心,則精不動而心易寂矣。
陳遠公曰:精出於水,亦出於水中之火也。精動由於火動,火不動則精安能搖乎?!可見精動由於心動也,心動之極則水火俱動矣。故安心為利精之法也。
救母篇第六
容成問于岐伯曰:天癸之水,男女皆有之,何以婦人經水謂之天癸乎?
岐伯曰:天癸水,壬癸之水也。壬水屬陽,癸水屬陰,二水者先天之水也。男為陽,女為陰,故婦人經水以天癸名之。其實壬癸未嘗不合也。
容成曰:男子之精,不以天癸名者,又何故歟?
岐伯曰:精者,合水火名之。水中有火,始成其精。呼精而壬癸之義已包於內,故不以天癸名之。
容成曰:精與經同一水也,何必兩名之?
岐伯曰:同中有異也。男之精,守而不溢;女之經,滿而必泄也。癸水者,海水也,上應月,下應潮,月有盈虧,潮有往來,女子之經水應之,故潮汐月有信,經水亦月有期也。以天癸名之,別其水為癸水,隨天運為轉移耳。
容成曰:其色赤者何也?
岐伯曰:男之精,陽中之陰也,其色白。女之經,陰中之陽也,其色赤。況流于任脈,通於血海,血與經合而成濁流矣。
容成曰:男之精虧而不溢者,又何也?
岐伯曰:女子陰有餘陽不足,故滿而必泄。男子陽有餘陰不足,故守而不溢也。
容成曰:味咸者何也?
岐伯曰:壬癸之水,海水也。海水味鹹,故天癸之味應之。
容成曰:女子二七經行,稚女不行經何也?
岐伯曰:女未二七則任沖未盛,陰氣未動,女猶純陽也,故不行經耳。
容成曰:女過二七,不行經而懷孕者,又何也?
岐伯曰:女之變者也,名為暗經,非無經也。無不足,無有餘,乃女中最貴者。終身不字,行調息之功,必長生也。
容成問曰:婦女經水,上應月,下應潮,宜月無愆期矣。何以有至有不至乎?
岐伯曰:人事之乖違也。天癸之水,生於先天,亦長於後天也。婦女縱欲傷任督之脈,則經水不應月矣。懷抱憂鬱以傷肝膽,則經水閉而不流矣。
容成曰:其故何也?
岐伯曰:人非水火不生,火乃腎中之真火,水乃腎中之真水也。水火盛則經盛,水火衰則經衰。任督脈通於腎,傷任督未有不傷腎者。交接時,縱欲泄精,精傷任督之脈亦傷矣。任督脈傷,不能行其氣於腰臍,則帶脈亦傷,經水有至有不至矣。夫經水者,火中之水也。水衰不能制火,則火炎水降,經水必先期至矣。火衰不能生水,則水寒火冷,經水必後期至矣。經水之愆期,因水火之盛衰也。
容成曰:肝膽傷而經閉者,謂何?
岐伯曰:肝藏血者也,然又最喜疏泄。膽與肝為表裏也,膽木氣鬱,肝木之氣亦鬱矣。木鬱不達,任沖血海皆抑塞不通,久則血枯矣。
容成曰:木鬱何以使水之閉也?
岐伯曰:心腎無咎不交者也。心腎之交接,責在胞胎,亦責在肝膽也。肝膽氣鬱,胞胎上交肝膽,不上交於心,則腎之氣亦不交於心矣。心腎之氣不交,各臟腑之氣抑塞不通,肝克脾,膽克胃,脾胃受克,失其生化之司,何能資於心腎乎?水火未濟,肝膽之氣愈鬱矣。肝膽久鬱,反現假旺之象,外若盛內實虛。腎因子虛轉去相濟涸水,而鬱火焚之,木安有餘波以下泄乎?此木鬱所以水閉也。
鬼臾區間曰:氣鬱則血閉,血即經乎?
岐伯曰:經水,非血也。
鬼臾區曰:經水非血,何以血閉而經即斷乎?
岐伯曰:經水者,天一之水也,出於腎經,故以經水名之。
鬼臾區曰:水出於腎,色宜白矣,何赤乎?
岐伯曰:經水者,至陰之精,有至陽之氣存焉,故色赤耳,非色赤即血也。
鬼臾區曰:人之腎有補無瀉,安有餘血乎?
岐伯曰:經水者,腎氣所化,非腎精所泄也。女子腎氣有餘,故變化無窮耳。
鬼臾區曰:氣能化血,各經之血不從之而泄乎?
岐伯曰:腎化為經,經化為血,各經氣血無不隨之而各化矣。是以腎氣通則血通,腎氣閉則血閉也。
鬼臾區曰:然則氣閉宜責在腎矣,何以心肝脾之氣鬱而經亦閉也?
岐伯曰:腎水之生,不由於三經。腎水之化,實關於三經也。
鬼臾區曰:何也?
岐伯曰:腎不通肝之氣,則腎氣不能開。腎不交心之氣,則腎氣不能上。腎不取脾之氣,則腎氣不能成。蓋交相合而交相化也。苟一經氣鬱,氣即不入於腎,而腎氣即閉矣。況三經同鬱,腎無所資,何能化氣而成經乎?是以經閉者,乃腎氣之鬱,非止肝血之枯也。倘徒補其血,則郁不宣反生火矣。徒散其瘀,則氣益微反耗精矣。非惟無益,而轉害之也。
鬼臾區曰:大哉言乎!請勒之金石,以救萬世之母乎。
陳遠公曰:一篇救母之文,真有益於母者也。講天癸無餘義,由於講水火無餘義也。水火之不通,半成於人氣之鬱。解鬱之法,在於通肝膽也,肝膽通則血何閉哉!正不必又去益腎也。誰知肝膽不鬱而腎受益乎,鬱之害亦大矣。
紅鉛損益篇第七
容成問曰:方士采紅鉛接命,可為訓乎?
歧天師曰:慎欲者采之,服食延壽;縱欲者采之,服食喪軀。
容成曰:人能慎欲命自可延,何藉紅鉛乎?
岐伯曰:紅鉛延景丹也。
容成曰:紅鉛者,天癸水也。雖包陰陽之水火,溢滿於外則水火之氣盡消矣,何以接命乎?
岐伯曰:公之言,論天癸則可,非論首經之紅鉛也。經水甫出戶輒色變,獨首經之色不遽變者,全其陰陽之氣也。男子陽在外,陰在內;女子陰在外,陽在內。首經者,坎中之陽也。以坎中之陽補離中之陰,益乎不益乎。獨補男有益,補女有損。補男者,陽以濟陰也;補女者,陽以亢陽也。
容成曰:善。
陳遠公曰:紅鉛何益於人,講無益而成有益者,辨其既濟之理也。誰謂方士非恃之以接命哉。
初生微論篇第八
容成問曰:人之初生,目不能睹,口不能餐,足不能履,舌不能語,三月而後見,八月而後食,期歲而後行,三年而後言,其故何也?
歧伯曰:人之初生,兩腎水火未旺也。三月而火乃盛,故兩目有光也。八月而水乃充,故兩齦有力也。期歲則髓旺而髕生矣。三年則精長而囟合矣。男十六天癸通,女十四天癸化。
容成曰:男以八為數,女以七為數,予知之矣。天師于二八二七之前,內經何未言也?
岐伯曰:內經首論天癸者,歎天癸難生易喪也。男必至十六而天癸滿,年未十六皆未滿之日也。女必至十四而天癸盈,年未十四皆末滿之日也。既滿既盈,又隨年俱耗,示人宜守此天癸也。
容成曰:男八八之後猶存,女七七之後仍在,似乎天癸之未盡也。天師何以七七、八八之後不再言之歟?
岐伯曰:予論常數耳,常之數可定,變之數不可定也。予所以論常不論變耳。
陳遠公曰:人生以天癸為主,有則生,無則死也。常變之說,惜此天癸也。二七、二八之論,亦可言而言之,非不可言而不言也。
骨陰篇第九
鳥師問于岐伯曰:嬰兒初生,無膝蓋骨,何也?
岐伯曰:嬰兒初生,不止無膝蓋骨也,囟骨、耳後完骨皆無之。
鳥師曰:何故也?
歧伯曰:陰氣不足也。陰氣者,真陰之氣也。嬰兒純陽無陰,食母乳而陰乃生,陰生而囟骨、耳後完骨、膝蓋骨生矣。生則兒壽,不生則夭。
鳥師曰:其不生何也?
歧伯曰:三骨屬陰,得陰則生,然亦必陽旺而長也。嬰兒陽氣不足,食母乳而三骨不生,其先天之陽氣虧也。陽氣先漓,先天已居於缺陷,食母之乳補後天而無餘,此三骨之所以不生也。三骨不生又焉能延齡乎!
鳥師曰:三骨缺一,亦能生乎?
岐伯曰:缺一則不全乎其人矣。
鳥師曰:請悉言之。
岐伯曰:因門不合則腦髓空也;完骨不長則腎宮虛也;膝蓋不生則雙足軟也。腦髓空則風易入矣;腎宮虛則聽失聰矣;雙足軟則顛僕多矣。
鳥師曰:吾見三骨不全亦有延齡者,又何故歟?
岐伯曰:三者之中,惟耳無完骨者亦有延齡,然而疾病不能無也。若囟門不合、膝蓋不生,吾未見有生者。蓋孤陽無陰也。
陳遠公曰:孤陽無陰,人則不生,則陰為陽之天也。無陰者無陽也。陽生於陰之中,陰長於陽之外,有三骨者,得陰陽之全也。
媾精受妊篇第十
雷公問曰:男女媾精而受妊者,何也?
岐伯曰:腎為作強之官,故受妊而生人也。
雷公曰:作強而何以生人也?
岐伯曰:生人者,即腎之技巧也。
雷公曰:技巧屬腎之水乎,火乎?
岐伯曰:水火無技巧也。
雷公曰:離水火又何以出技巧乎?
岐伯曰:技巧成於水火之氣也。
雷公曰:同是水火之氣,何生人有男女之別乎?
岐伯曰:水火氣弱則生女,水火氣強則生男。
雷公曰:古雲:女先泄精則成男,男先泄精則成女。今曰:水火氣弱則生女,水火氣強則生男。何也?
岐伯曰:男女俱有水火之氣也,氣同至則技巧出焉,一有先後不成胎矣。男泄精,女洩氣,女子泄精則氣脫矣,男子洩氣則精脫矣,烏能成胎?!
雷公曰:女不泄精,男不洩氣,何以受妊乎?
岐伯曰:女氣中有精,男精中有氣,女洩氣而交男子之精,男泄精而合女子之氣,此技巧之所以出也。
雷公曰:所生男女,有強有弱,自分于父母之氣矣。但有清濁壽夭之異,何也?
岐伯曰:氣清則清,氣濁則濁,氣長則壽,氣促則夭。皆本子父母之氣也。
雷公曰:生育本於腎中之氣,餘已知之矣。但此氣也,豫於五臟七腑之氣乎?
岐伯曰:五臟七腑之氣,一經不至皆不成胎。
雷公曰:媾精者,動腎中之氣也。與五臟七腑何豫乎?
岐伯曰:腎藏精,亦藏氣。藏精者,藏五臟七腑之精也。藏氣者,藏五臟七腑之氣也。藏則俱藏,泄則俱泄。
雷公曰:洩氣者,亦泄血乎?
岐伯曰:精即血也。氣無形?血有形,無形化有形,有形不能化無形也。
雷公曰:精非有形乎?
岐伯曰:精雖有形,而精中之氣正無形也。無形隱於有形,故能靜能動。動則化耳,化則技巧出矣。
雷公曰:微哉言乎,請傳之奕祀,以彰化育焉。
陳士鐸曰:男女不媾精,斷不成胎。胎成於水火之氣,此氣即男女之氣也。氣藏於精中,精雖有形而實無形也。形非氣乎,故成胎即成氣之謂。
社生篇第十一
少師問曰:人生而白頭,何也?
岐伯曰:社日生人,皮毛皆、白,非止髩發之白也。
少師曰:何故乎?
岐伯曰:社日者,金日也。皮毛須髩皆白者,得金之氣也。
少師曰:社日非金也,天師謂之金日,此餘之未明也。
岐伯曰:社本土也,氣屬金,社日生人犯金之氣。金氣者,殺氣也。
少師曰:人犯殺氣,宜天矣,何又長年乎?
岐伯曰:金中有土,土乃生氣也。人肺屬金,皮毛亦屬金,金之殺氣得土則生,逢金則鬥。社之金氣伐人皮毛,不入人臟腑,故得長年耳。
少師曰:社日生人皮毛髩發不盡白者,又何故歟?
岐伯曰:生時不同也。
少師曰:何時乎?
岐伯曰:非己午時,必辰戌醜未時也。
少師曰:巳午火也,火能制金之氣,宜矣。辰戌醜未土也,不助金之氣乎?
岐伯曰:社本土也,喜生惡泄,得土則生,生則不克矣。
少師曰:同是日也,何社日之凶如是乎?
岐伯曰:歲月日時俱有神司之,社日之神與人最親,其性最喜潔也,生產則穢矣。兩氣相感,兒身受之,非其煞之暴也。
少師曰:人生有記,赤如朱,青如靛,黑如鍋,白如雪,終身不散,何也?豈亦社日之故乎?
岐伯曰:父母交媾,偶犯遊神,為神所指,志父母之,過也。
少師曰:色不同者,何歟?
岐伯曰:隨神之氣異也。
少師曰:記無黃色者,何也?
岐伯曰:黃乃正色,人犯正神,不相校也,故亦不相指,不相指,故罔所記耳。
陳遠公曰:社日生人,說來有源有委,非孟浪成文者可比。
天厭火衰篇第十二
容成問曰:世有天生男子音聲如女子,外勢如嬰兒,此何故歟?
岐伯曰:天厭之也。
容成曰:天何以厭之乎?
岐伯曰:天地有缺陷,安得人盡皆全乎?
容成曰:天未嘗厭人,奈何以天厭名之。
岐伯曰:天不厭而人必厭也,天人一道,人厭即天厭矣。
容成曰:人何不幸成天厭也了?
岐伯曰:父母之咎也。人道交感,先火動而後水濟之,火盛者生子必強,火衰者生子必弱,水盛者生子必肥,水衰者生子必瘦。天厭之人,乃先天之火微也。
容成曰:水火衰盛分強弱肥瘦,宜也,不宜外陽之細小。
岐伯曰:腎中之火,先天之火,無形之火也。腎中之水,先天之水,無形之水也。火得水而生,水得火而長,言腎內之陰陽也。水長火,則水為火之母;火生水,則火為水之母也。人得水火之氣以生身,則水火即人之父母也。天下有形不能生無形也,無形實生有形。外陽之生,實內陽之長也。內陽旺而外陽必伸,內陽旺者得火氣之全也。內陽衰矣,外陽亦何得壯大哉?
容成曰:火既不全,何以生身乎?
岐伯曰:孤陰不生,孤陽不長。天厭之人,但火不全耳,未嘗無陰陽也;偏于火者,陽有餘而陰不足,偏于水者,陰有餘而陽不足也。陽既不足,即不能生厥陰之宗筋,此外陽之所以屈而不伸也,毋論剛大矣。
容成曰:善。
陳遠公曰:外陽之大小,視水火之偏全,不視陰陽之有無耳。說來可聽。
經脈相行篇第十三
雷公問曰:帝問脈行之逆順若何,餘無以奏也。願天師明教以聞。
岐伯曰:十二經脈有自上行下者,有自下行上者,各不同也。
雷公曰:請悉言之。
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臟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此上下相行之數也。
雷公曰:尚未明也。
岐伯曰:手之三陰:太陰肺,少陰心,厥陰包絡也。手太陰從中府走大指之少商,手少陰從極泉走小指之少沖,手厥陰從天池走中指之中沖。皆從臟走手也。手之三陽:陽明大腸,太陽小腸,少陽三焦也。手陽明從次指商陽走頭之迎香,手太陰從小指少澤走頭之聽宮,手少陽從四指關沖走頭之絲竹空,皆從手走頭也。足之三陽:太陽膀胱,陽明胃,少陽膽也。足太陽從頭睛明走足小指之至陰,足陽明從頭頭維走足次指之厲兌,足少陽從頭前關走四指之竅陰,皆從頭走足也。足之三陰:太陰脾,少陰腎,厥陰肝也。足太陰從足大指內側隱白走腹之大包,足少陰從足心湧泉走腹之俞府,足厥陰從足大指外側大敦走腹之期門,皆從足走腹也。
雷公曰:逆順若何?
岐伯曰:手之陰經,走手為順,走臟為逆也;手之陽經,走頭為順,走手為逆也;足之陰經,走腹為順,走足為逆也;足之陽經,走足為順,走頭為逆也。
雷公曰:足之三陰,皆走於腹,獨少陰之脈下行,何也?豈少陰經易逆難順乎?
岐伯曰:不然,天沖脈者,五藏六腑之海也。五藏六腑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下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沖,循陰陽內廉入胭中,伏行(骨行)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由少陰經滲三陰,其在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邪結則跗上脈不動,不動則厥,厥則足寒矣。此足少陰之脈少異于三陰而走腹則一也。
雷公曰:其少異于三陰者為何?
岐伯曰:少陰腎經中藏水火,不可不曲折以行,其脈不若肝脾之可直行於腹也。
雷公曰:其走腹則一者何?
岐伯曰:腎之性喜逆行,故由下而上,蓋以逆為順也。
雷公曰:逆行宜病矣。
岐伯曰:逆而順故不病,若順走是違其性矣,反生病也。
雷公曰:當盡奏之。
岐伯曰:帝問何以明之?
公奏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髁必動。乃可以驗逆順之行也。
雷公曰:謹奉教以聞。
陳遠公曰:十二經脈有走手、走足、走頭、走腹之異,各講得鑿鑿。其講順逆不同處,何人敢措一辭。
經脈終始篇第十四
雷公問于岐伯曰:十二經之脈既有終始,《靈》《素》詳言之。而走頭、走腹、走足、走手之義,尚未明也,願畢其辭。
岐伯曰:手三陽從手走頭,足三陽從頭走足,乃高之接下也。足三陰從足走腹,手三陰從腹走手,乃卑之趨上也。陰陽無間,故上下相迎,高卑相迓,與晝夜迴圈同流而不定耳。夫陰陽者,人身之夫婦也;氣血者,人身之陰陽也。夫倡則婦隨,氣行則血赴,氣主煦之,血主濡之。乾作天門,大腸司其事也。巽作地戶,膽持其權也。泰居艮,小腸之昌也。否居坤,胃之殃也。
雷公曰;善,請言順逆之別。
岐伯曰:足三陰自足走腹,順也;自腹走足,逆也。足三陽自頭走足,順也;自足走頭,逆也。手三陰自藏走手,順也;自手走藏,逆也。手三陽自手走頭,順也;自頭走手,逆也。夫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惟足少陰腎脈繞而下行,與肝脾直行者,以沖脈與之並行也,是以逆為順也。
陳遠公曰:十二經有頭腹手足之殊,有順中之逆,有逆中之順,說得更為明白。
經氣本標篇第十五
雷公問于岐伯曰:十二經氣有標本乎?
岐伯曰:有之。
雷公曰:請言標本之所在。
岐伯曰: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三寸中,標在背腧。足厥陰之奉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中,標在舌本乎。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顏下合鉗上。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中,標在腋內動脈。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此標本之所在也。
雷公曰:標本皆可刺乎?
岐伯曰:氣之標本皆不可刺也。
雷公曰;其不可剌,何也?
岐伯曰;氣各有沖,沖不可刺也。
雷公曰:請言氣沖。
岐伯曰:胃氣有沖,腹氣有沖,頭氣有沖,脛氣有沖,皆不可剌也。
雷公曰:頭之沖何所乎?
岐伯曰:頭之沖,腦也。
雷公曰:胸之沖何所乎?
岐伯曰:胸之沖,膺與背腧也。喻亦不可剌也。
雷公曰:腹之沖何所乎?
岐伯曰:腹之沖,背腧與沖脈及左右之動脈也。
雷公曰:脛之沖何所乎?
岐伯曰:脛之沖,即臍之氣街及承山踝上以下。此皆不可刺也。
雷公曰:不可刺止此乎?
岐伯曰: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胸中,藏於氣海,出於肺,循咽喉,呼吸而出入也。是氣海猶氣街也,應天地之大數,出三入一,皆不可剌也。
陳遠公曰:十二經氣各有標本,各不可剌。不可刺者,以沖脈之不可剌也。不知沖脈即不知刺法也。
臟腑闡微篇第十六
雷公問于岐伯曰:臟止五乎?腑止六乎?
岐伯曰:臟六腑七也。
雷公曰:臟六何以名五也?
岐伯曰:心肝脾肺腎五行之正也,故名五臟。胞胎非五行之正也,雖臟不以臟名之。
雷公曰:胞胎何以非五臟之正也?
岐伯曰:心火也,肝木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一臟各屬一行。胞胎處水火之歧;非正也,故不可稱六臟也。
雷公曰:腎中有火亦水火之歧也,何腎稱臟乎?
岐伯曰:腎中之火先天火也,居兩腎中而腎專司水也。胞胎上系心,下連腎,往來心腎,接續於水火之際,可名為火,亦可名為水,非水火之正也。
雷公曰:然則胞胎何以為臟乎?
岐伯曰:胞胎處水火之兩歧,心腎之交,非胞胎之系不能通達上下,寧獨婦人有之,男子未嘗無也。吾因其兩歧,置於五臟之外,非胞胎之不為臟也。
雷公曰:男女各有之,亦有異乎?
岐伯曰:系同而口異也。男女無此系,則水火不交,受病同也。女系無口,則不能受妊,是胞胎者,生生之機,屬陰而藏于陽,非臟而何。
雷公曰:胞胎之口又何以異?
岐伯曰:胞胎之系,上出於心之膜膈,下連兩腎,此男女之同也。惟女下大而上細,上無口而下有口,故能納精以受妊。
雷公曰:腑七而名六何也?
岐伯曰:大小腸、膀胱、膽、胃、三焦、包絡,此七腑也。遺包絡不稱腑者,尊帝耳。
雷公曰;包絡可遺乎?
岐伯曰:不可遺也。包絡為脾胃之母,土非火不生。五臟六腑之氣咸仰於心君,心火無為,必藉包絡有為,往來宣佈胃氣,能入脾氣,能出各臟腑之氣,始能變化也。
雷公曰:包絡既為一腑,奈何尊帝遺之。尊心為君火,稱包絡為相火,可乎?
請登之《外經》鹹以為則。
陳遠公曰:臟六而言五者,言臟之正也。腑七而言六者,言腑之偏也。舉五而略六,非不知胞胎也;舉六而略七,非不知包絡也。有雷公之間,而胞胎包絡昭於古今矣。
考訂經脈篇第十七
雷公問于岐伯曰:十二經脈天師詳之,而所以往來相通之故,尚來盡也。幸宣明奧義,傳諸奕祀可乎?
岐伯曰:可,肺屬手太陰,太陰者,月之象也,月屬金,肺亦屬金。肺之脈走於手,故曰手太陰也。起於中焦胃脘之上,胃屬土,土能生金,是胃乃肺之母也。下絡大腸者,以大腸亦屬金,為胃之庶於,而肺為大腸之兄,兄能包弟,足以網羅之也。絡即網羅包舉之義。循於胃口者,以胃為肺之母,自必游熙於母家,省受胃土之氣也。肺脈又上於膈,胃之氣多,必分氣以給其子,肺得胃母之氣,上歸肺宮,必由膈而升肺。受胃之氣肺自成家,於是由中焦而脈乃行,橫出腋下,畏心而不敢犯也。然而肺之系實通於心,以心為肺之君,而肺乃臣也,臣必朝於君,此述職之路也。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者,又謁相之門也。心主即心包絡,為心君之相,包絡代君以行事。心克肺金,必借心主之氣以相刑。呼吸相通,全在此系之相聯也。肺稟天玉之尊,必奉宰輔之令,所以行于少陰心主之前而不敢緩也。自此而下,幹肘中乃走於臂,由臂而走於寸口魚際,皆肺脈相通之道。循魚際出大指之端,為肺脈之盡。經脈盡,複行,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乃旁出之脈也。
雷公曰:脾經若何了?
岐伯曰:脾乃土臟,其性濕,以足太陰名之。太陰之月,夜照於土,月乃陰象,脾屬土,得月之陰氣,故乙太陰名之。其脈起於足之大指端,故又曰足太陰也。脾脈既起於足下,下必升上,由足大指內側肉際,過橫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乃入肝經之路也。夫肝木克脾,宜為脾之所畏,何故脈反通於肝,不知肝雖克土,而木亦能成土,土無木氣之通,則土少發生之氣,所以畏肝而又未嘗不喜肝也。交出足厥陰之前,圖合於肝木耳。上膝肢內前廉入腹者,歸於睥經之本臟也。蓋腹,脾之正宮,睥厲土居於中州,中州為天下之腹,脾乃人一身之腹也。脾與胃為表裏,脾內而胃外,脾為胃所包,故絡於胃。脾得胃氣則脾之氣始能上升,故脈亦隨之上鬲,趨喉嚨而至舌本,以舌本為心之苗,而脾為心之子,子母之氣自相通而不隔也。然而舌為心之外竅,非心之內廷也,脾之脈雖至於舌,而終未至於心,故其支又行,借胃之氣從胃中中脘之外上鬲,而脈通於膻中之分,上交于手少陰心經,子親母之象也。
雷公曰:心經若何?
岐伯曰:心為火臟,以手少陰名之者,蓋心火乃後天也。後天者,有形之火也。星應熒惑,雖屬火而實屬陰,且脈走於手,故以手少陰名之。他臟腑之脈皆起於手足,心脈獨起於心,不與眾脈同者,以心為君主,總攬權綱,不寄其任於四末也。心之系,五臟七腑無不相通,尤通者小腸也。小腸為心之表,而心實絡於小腸,下通任脈,故任脈即借小腸之氣以上通於心,為朝君之象也。心之系又上與肺相通,挾咽喉而入於目,以發其文明之彩也。複從心系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厥陰經心主之後,下肘,循臂至小指之內出其端,此心脈系之直行也。又由肺曲折而後,並脊直下,與腎相貫串,當命門之中,此心腎既濟之路也。夫心為火臟,懼畏水克,何故系通於腎,使腎有路以相犯乎?不知心火與命門之火原不可一日不相通也,心得命門之火則心火有根,心非腎水之滋則心火不旺。蓋心火必得腎中水火以相養,是以克為生也。既有腎火腎水之相生,而後心之系各通臟腑,無擀格之憂矣。由是而左通於肝,肝本屬木,為生心之母也。心火雖生於命門先天之火,而非後天肝木培之則先天之火氣亦不旺,故心之系通於肝者,亦欲得肝木相生之氣也。肝氣既通,而膽在肝之旁,通肝即通於膽,又勢之甚便者,況膽又為心之父,同本之親尤無阻隔也。由是而通於脾,脾乃心之子也,雖脾土不藉心火之生,然胃為心之愛子,胃土非心火不生,心既生胃,生胃必生脾,此脾胃之系所以相接而無間也。由是而通於肺,火性炎上,而肺葉當之,得母有傷,然而頑金非火不柔,克中亦有生之象,倘肺金無火則金寒水冷,胃與膀胱之化源絕矣,何以溫腎而傳化於大腸乎。由是而通於心主,心主即膻中包絡也,為心君之相臣,奉心君以司化,其出入之經,較五臟六腑近,真有心喜亦喜,心憂亦憂之象,呼吸相通,代君司化以使令夫三焦,俾上中下之氣無不畢達,實心之系通之也。
雷公曰:腎經若何?
岐伯曰:腎屬水,少陰正水之象。海水者,少陰水也,隨月為盈虛,而腎應之。名之為足少陰者,脈起于足少陰之下也,由足心而上,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上膊出膕上股貫脊,乃河車之路,即任督之路也。然俱屬於腎,有腎水而河車之路通,無腎水而河車之路塞,有腎水而督脈之路行,無腎水而督脈之路斷,是二經之相通相行,全責於腎,故河車之路、督脈之路,即腎經之路也。由是而行於肝,母入於子舍之義也。由是而行于脾,水行於地中之義也。過肝脾二經而絡於膀胱者,以腎為膀胱之裏,而膀胱為腎之表,膀胱得腎氣而始化,正同此路之相通,氣得以往來之耳。其絡於膀胱也,貫脊會督而還出於臍之前,通任脈始得達於膀胱,雖氣化可至,實有經可通而通之也。其直行者,又由肝以入肺,子歸母之家也。由肺而上循喉嚨,挾舌本而終,是欲朝君先通於喉舌也。夫腎與心雖若相克而實相生,故其系別出而繞於心,又未敢遽朝於心君,注胸之膻中包絡而後,腎經之精上奉,化為心之液矣,此君王下取于民之義,亦草野上貢于國之誼也。各臟止有一而腎有二者,兩儀之象也。兩儀者,日月也。月主陰,日主陽,似腎乃水臟宜應月不宜應日,然而月之中未嘗無陽之氣,日之中未嘗無陰之氣,腎配日月正以其中之有陰陽也。陰藏于陽之中,陽隱于陰之內,疊相為用,不啻日月之照臨也.蓋五臟七腑各有水火,獨腎臟之水火處於無形,乃先天之水火,非若各臟腑之水火俱屬後天也。夫同是水火,腎獨屬之先天,實有主以存乎兩腎之間也。主者,命門也。命門為小心,若太極之象能生先天之水火,因以生後天之水火也。於是裁成夫五臟七腑,各安于諸宮,享其奠定之福,化生於無窮耳。
雷公曰:肝經若何?
岐伯曰:肝屬足厥陰。厥陰者,逆陰也,上應雷火。脈起足大指叢毛之際,故以足厥陰名之。雷火皆從地起,騰於天之上,其性急,不可制抑,肝之性亦急,乃陰經中之最逆者,少拂其意,則厥逆而不可止。循跗上上踝,交出太陰脾土之後,上胭內廉,循腹入陰毛中,過陰器,以抵於小腹,雖趨肝之路,亦趨脾之路也。既趨於脾,必趨於胃矣。肝之系既通於脾胃,凡有所逆,必先犯於脾胃矣,亦其途路之熟也。雖然,肝之系通於脾胃,而肝之氣必歸於本宮,故其系又走于肝葉之中,肝葉之旁有膽附焉,膽為肝之兄,肝為膽之弟,膽不絡肝而肝反絡膽者,弟強于兄之義也。上貫膈者,趨心之路也。肝性急,宜直走于心之宮矣,乃不直走於心,反走膜鬲,布於脅肋之間者,母慈之義也。慈母憐子必為子多方曲折,以厚其藏,脅肋正心宮之倉庫也,然而其性正急,不能久安於脅肋之間,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於目系,上出額間而會督脈于巔項,乃木火升上之路也。其支者,從目系下頰環唇,欲隨口舌之竅以泄肝木之鬱火也。其支者,又從肝別貫膈,上注肺中,畏肺金之克木,通此經為偵探之途也。
雷公曰:五臟已知其旨矣。請詳言七腑。
岐伯曰:胃經亦稱陽明者,以其脈接大腸手陽明之脈,由鼻額而下走於足也。然而胃經屬陽明者,又非同大腸之謂。胃乃多氣多血之腑,實有日月並明之象,乃純陽之腑,主受而又主化也。陽主上升,由額而遊行於齒口唇吻,循頤頰耳前而會於額顱,以顯其陽之無不到也。其支別者,從頤後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行足少陰之外,下隔通腎與心包之氣。蓋胃為腎之關,又為心包之用,得氣於二經,胃始能蒸腐水穀以化精微也。胃既得二經之氣,必歸於胃中,故仍屬胃也。胃之旁絡於脾,胃為脾之夫,脾為胃之婦,脾聽胃使,以行其運化者也。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挾臍而入氣街。氣街者,氣沖之穴也,乃生氣之源,探源而後,氣充於乳房,始能散佈各經絡也。其支者,起於胃口,循腹過足少陰腎經之外,本經之裏下至氣街而合,仍是取氣於腎,以助其生氣之源也。由是而胃既得氣之本,乃可下行,以達於足。從氣街而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循脛下跗,入中指之內庭而終者,皆胃下達之路也。其支者,從膝之下廉三寸,別入中指之外間,複是旁行之路,正見其多氣多血,無往不周也。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問,出足厥陰,交于足太陰,避肝木之克,近脾土之氣也。
雷公曰:請言三焦之經。
岐伯曰;三焦屬之手少陽者,以三焦無形,得膽木少陽之氣,以生其火而脈起於手之小指次指之端,故以手少陽名之。循手腕出臂貫肘,循層之外,行手太陽之裏,手陽明之外,火氣欲通於大小腸也。上肩循臂臑,交出足少陽之後,正倚附於膽木以取其木中之火也。下缺盆,由足陽明之外面交會於膻中;之上焦,散佈其氣而絡繞於心包絡;之中焦,又下膈入絡膀胱以約下焦。若胃若心包絡若膀胱,皆三焦之氣往?來於上中下之際,故不分屬於三經而仍專屬於三焦也。然而三焦之氣雖往來於上中下之際,使無根以為主,則氣亦時聚時散,不可久矣。詎知三焦雖得膽木之氣以生,而非命門之火則不長。三焦有命門以為根而後,布氣於胃,則胃始有運用之機;布氣於心包絡,則心包絡始有運行之權;布氣於膀胱,則膀胱始有運化之柄也。其支者,從膻中而上,出缺盆之外,土項系耳後,直上出耳上角至顓,無非隨腎之火氣而上行也。其支者,又從耳後入耳中,出耳前,過客主人之穴,交頰至目銳眥,亦火性上炎,隨心包之氣上行。然目銳眥實系膽經之穴,仍欲依附木氣以生火氣耳。
雷公曰:請言心主之經。
岐伯曰:心主之經即包絡之府也,又名膻中。屬手厥陰者,以其代君出治,為心君之相臣,臣乃陰象,故屬陰。然奉君令以出治,有不敢少安於頃刻,故其性又急,與肝木之性正相同,亦以厥陰名之,因其難順而易逆也。夫心之脈出於心之本宮,心包絡之脈出於胸中,包絡在心之外,正在胸之中,是脈出於胸中者,正其脈屬於包絡之本宮也。各臟腑脈出於外,心與包絡脈出於中,是二經較各臟腑最尊也。夫腎系交於心包絡,實與腎相接,蓋心主之氣與腎宮命門之氣同氣相合,故相親而不相離也。由是下於膈,曆絡三焦,以三焦之腑氣與命門心主之氣彼此實未嘗異,所以籠絡而相合為一,有表裏之名,實無表裏也。其支者,循胸中出脅抵腋,循屬內行于太陰肺脾少陰心腎之中,取肺腎之氣以生心液也。入脈下臂,入掌內,又循中指以出其端。其支者,又由掌中循無名指以出其端,與少陽三焦之脈相交會,正顯其同氣相親,表裏如一也。夫心主與三焦兩經也,必統言其相合者,蓋三焦無形。借心主之氣相通於上中下之間,故離心主無以見三焦之用,所以必合而言之也。
雷公曰:請言膽經。
岐伯曰:膽經屬足少陽者,以膽之脈得春木初陽之氣,而又下趨於足,故以足少陽名之。然膽之脈雖趨於足,而實起目之銳眥,接手少陽三焦之經也。由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循頸,行手少陽之脈前,至肩上,交出手少陽之後,以入缺盆之外,無非助三焦之火氣也。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之後,雖旁出其支,實亦仍顧三焦之脈也。其支者,別自目外而下大迎,合手少陽三焦,抵於(出頁),下頸,複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膜、膈、心包絡,以絡于肝,蓋心包絡乃膽之子,而肝乃膽之弟,故相親而相近也。第膽雖肝之兄,而附於肝,實為肝之表,而屬於膽。肝膽兄弟之分,即表裏之別也。膽分肝之氣,則膽之汁始旺,膽之氣始張,而後可以分氣於兩脅,出氣街,統毛際而橫入髀厭之中也。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與前之入髀厭者相合,乃下循髀外,行太陽陽明之間,欲竊水土之氣以自養也。出膝外廉,下肋骨以直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循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乃其直行之路也。其支者,又別跗上,入大指歧骨內出其端,還貫入爪甲,出三毛,以交于足厥陰之脈,親肝木之氣以自旺,蓋陽得陰而生也。
雷公曰:請言膀胱之經。
岐伯曰:膀胱之經屬足太陽者,蓋太陽為巨陽,上應於日,膀胱得日之火氣,下走於足,猶太陽火光普照於地也。其脈起目內眥,交手太陽小腸之經,受其火氣也。上額交巔,至耳上角,皆火性之炎上也。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膊內挾脊兩旁下行,抵於腰,入循膂絡腎,蓋膀胱為腎之表,故系連於腎,通腎中命門之氣,取其氣以歸膀胱之中,始能氣化而出小便也。雖氣出於腎經,而其系要不可不屬之膀胱也。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以貫臀,入胭中而止,亦借腎氣下達之也。其支者,從膊內別行下貫脾膂,下曆尻臀,化小便通陰之器而下出也。過髀樞,循髀外下合胭中,下貫於兩踹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交于足少陰之腎經,亦取腎之氣可由下面升,以上化其水也。
雷公曰:請言小腸之經。
岐伯曰:小腸之經屬手太陽者,以脈起於手之小指,又得心火之氣而名之也。夫心火屬少陰,得心火之氣,宜稱陰矣。然而心火居於內者為陰,發於外者為陽,小腸為心之表也,故稱陽而不稱陰,且其性原眉陽,得太陽之日氣,故亦以太陽名之。其脈上腕出踝,循臂出肘,循履行手陽明少陽之外,與太陽膽氣相通,欲得金氣自寒,欲得木氣自生也。交肩上,入缺盆,循肩向腋下行,當膻中而絡於心,合君相二火之氣也。循咽下膈以抵於胃,雖火能生胃,而小腸主出不主生,何以抵胃,蓋受胃之氣,運化精微而生糟粕,猶之生胃也。故接胃之氣,下行任脈之外,以自歸於小腸之正宮,非小腸之屬而誰屬乎。其支者,從缺盆循頸頰上至目銳眥,入於耳中,此亦火性炎上,欲趨竅而出也。其支者,別循頰上頗,抵鼻至目內;眥,斜絡於顴,以交足太陽膀胱之經,蓋陽以趨陽之應也。
雷公曰:請言大腸之經。
岐伯曰:大腸之經名為手陽明者,以大腸職司傳化,有顯明昭著之意,陽之象也。夫大腸屬金,宜為陰象,不屬陰而屬陽者,因其主出而不主藏也。起於手大指次指之端,故亦以手名之。循指而入於臂,入肘上臑,上肩下入缺盆而絡於肺,以肺之氣能包舉大腸,而大腸之系亦上絡於肺也。大腸得肺氣而易於傳化,故其氣不能久留於膈中,而系亦下膈,直趨大腸以安其傳化之職。夫大腸之能開能闔,腎主之,是大腸之氣化宜通于腎,何-以大腸之系絕,不與腎會乎。不知肺金之氣即腎中水火之氣也,腎之氣必來於肺中,而肺中之氣既降於大腸之內,則腎之氣安有不入於大腸之中者乎。不必更有系通腎,而後得其水火之氣,始能傳化而開合之也。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縫中,還出夾兩口吻,交於唇中之左右,上挾鼻孔,正顯其得肺腎之氣,隨肺腎之脈而上升之征也。
陳遠公曰:十二經脈各說得詳盡,不必逐段論之。
包絡配腑篇第十八
天老問于岐伯曰:天有六氣,化生地之五行,地有五行,化生人之五臟。有五臟之陰,即宜有五腑之陽矣,何以臟止五,腑有七也?
岐伯曰:心包絡,腑也,性屬陰,故與臟氣相同,所以分配六腑也。
天老曰:心包絡既分配腑矣,是心包絡即臟也,何不名臟而必別之為腑耶?
岐伯曰:心包絡,非臟也。
天老曰:非臟列於臟中,毋乃不可乎?
岐伯曰:臟稱五不稱六,是不以臟予包絡也。腑稱六,不稱七,是不以腑名包絡也。
天老曰:心包絡,非臟非腑何以與三焦相合乎?
岐伯曰:包絡與三焦為表裏,二經皆有名無形,五臟有形與形相合,包絡無形,故與無形相合也。
天老曰:三焦為孤臟,既名為臟,豈合于包絡乎?
岐伯曰:三焦雖亦稱臟,然孤而寡合,仍是腑非臟也,舍包絡之氣,實無可依,天然配合,非勉強附會也。
天老曰:善。
雷公曰:肺合大腸,心合小腸,肝合膽,脾合胃,腎合膀胱,此天合也。三焦與心包絡相合,恐非天合矣。
岐伯曰:包絡非臟而與三焦合者,包絡裏三焦表也。
雷公曰:三焦腑也,何分表裏乎?
岐伯曰:三焦之氣,本與腎親,親腎不合腎者,以腎有水氣也。故不合腎而合于包絡耳。
雷公曰:包絡之火氣出於腎,三焦取火於腎,不勝取火于包絡乎。
岐伯曰:膀胱與腎為表裏,則腎之火氣必親膀胱而疏三焦矣。包絡得腎之火氣,自成其腑,代心宣化,雖腑猶臟也。包絡無他腑之附,得三焦之依而親,是以三焦樂為表,包絡亦自安於裏,孤者不孤,自合者永合也。
雷公曰:善。
應龍問曰:包絡腑也,三焦亦自成腑,何以為包絡之使乎?
岐伯曰:包絡即膻中也,為心膜鬲,近于心宮,遮護君主,其位最親,其權最重,故三焦奉令不敢後也。
應龍曰:包絡代心宣化,宜各臟腑皆奉令矣,何獨使三焦乎了?
岐伯曰:各腑皆有表裏,故不聽包絡之使,惟三焦無臟為表裏,故包絡可以使之。
應龍曰:三焦何樂為包絡使乎?
岐伯曰:包絡代心出治,腑與臟同,三焦聽使于包絡,猶聽使於心,故包絡為裏,三焦為表,豈勉強附會哉。
應龍曰:善。
陳士鐸曰:包絡之合三焦,非無因之合也。包絡之使三焦,因其合而使;之也,然合者,仍合於心耳,非包絡之司為合也。
膽腑命名篇第十九
胡孔甲問于岐伯曰:大腸者,白腸也,小腸者,赤腸也,膽非腸,何謂青腸乎?
歧伯曰:膽貯青汁,有入無出,然非腸何能通而貯之乎,故亦以腸名之。青者,木之色,膽屬木,其色青,故又名青腸也。
胡孔甲曰:十一臟取決於膽,是腑亦有臟名矣,何臟分五而腑分七也?
岐伯曰:十一臟取決於膽,乃省文耳,非腑可名臟也。
孔甲曰:膽既名為臟,而十一臟取決之,固何所取之乎?
岐天師曰:膽司滲,凡十一臟之氣得膽氣滲之,則分清化濁,有奇功焉。
孔甲曰:膽有入無出,是滲主入而不主出也,何能化濁乎?
岐伯曰:清滲入則濁自化,濁自化而清亦化矣。
孔甲曰:清滲入而能化,是滲入而仍滲出矣。
岐伯曰:膽為清淨之府。滲入者,清氣也,遇清氣之臟腑亦以清氣應之,應即滲之機矣,然終非滲也。
孔甲曰:臟腑皆取決於膽,何臟腑受膽之滲乎?
岐伯曰:大小腸膀胱皆受之,而膀胱獨多焉,雖然膀胱分膽之滲,而膽之氣虛矣。膽虛則膽得滲之禍矣,故膽旺則滲益,膽虛則滲損。
孔甲曰:膽滲何氣則受損乎?
岐伯曰:酒熱之氣,膽之所畏也,過多則滲失所司,膽受損矣,非毒結於腦則涕流於鼻也。
孔甲曰:何以治之?
岐伯曰:剌膽絡之穴,則病可已也。
孔甲曰:善。
陳士鐸曰:膽主滲,十二臟皆取決於膽者,正決於滲也。膽不能滲又何取決乎。
任督死生篇第二十
雷公問曰:十二經脈之外,有任督二脈,何略而不言也?
岐伯曰:二經之脈不可略也。以二經散見於各經,故言十二經脈而二經已統會於中矣。
雷公曰:試分言之。
岐伯曰:任脈行胸之前,督脈行背之後也。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嚨上頤,循面入目眥,此任脈之經絡也。督脈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在溺孔之際,其絡循陰器合纂間,統纂後,即前後二陰之間也,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至鼻柱,還出別下項,循肩膊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纂,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系兩目之下中央,此督脈之經絡也。雖督脈止於齦交,任脈止於承漿,其實二脈同起於會陰。止於齦交者未嘗不過承漿,止於承漿者未嘗不過齦交,行於前者亦行於後,行於後者亦行於前,迴圈周流彼此無間,故任督分之為二,合之仍一也。夫會陰者,至陰之所也。任脈由陽行于陰,故脈名陰海。督脈由陰行于陽,故脈名陽海。非齦交穴為陽海,承漿穴為陰海也。陰交陽而陰氣生,陽交陰而陽氣生,任督交而陰陽自長,不如海之難量乎,故以海名之。
雷公曰:二經之脈絡予已知之矣。請問其受病何如?
岐伯曰:二經氣行則十二經之氣通,二經氣閉則十二經之氣塞,男則成疝,女則成瘕,非遺溺即脊強也。
雷公曰:病止此乎?
岐伯曰:腎之氣必假道、于任督二經,氣閉則腎氣塞矣。女不受妊,男不射精,人道絕矣。然則任督二經之脈絡,即人死生之道路也。
雷公曰:神哉論也。請載《外經》,以補《內經》未備。
陳士鐸曰:任督之路,實人生死之途。說得精好入神。
陰陽二蹺篇第二十一
司馬問曰:奇經八脈中有陰蹺陽蹺之脈,可得聞乎?
岐伯曰:《內經》言之矣。
司馬曰:《內經》言之,治病未驗或有未全歟。
岐伯曰:《內經》約言之,實未全也。陰蹺脈足少陰腎經之別脈也,起於然骨之照海穴,出內踝上,又直上之,循陰股以入于陰,上循胸裏,入於缺盆,上出入迎之前,入於目下鳩,屬於目眥之睛明穴,合足太陽膀胱之陽蹺而上行,此陰蹺之脈也。陽蹺脈足太陽膀胱之別脈也,亦起於然骨之下申脈穴,出外踝下,循僕參,郤于附陽,與足少陽會于居髎,又與手陽明會於肩髃及巨骨,又與手太陽陽維會于臑俞,與手足陽明會於地倉及巨髎,與任脈足陽明會於承泣,合足少陰腎經之陰蹺下行,此陽蹺之脈也。然而蹺脈之起止,陽始於膀胱而止于腎,陰始於腎而止於膀胱,此男子同然也,若女子微有異。男之陰蹺起於然骨,女之陰蹺起于陰股;男之陽蹺起于申脈,女之陽蹺起於僕參。知同而治同,知異而療異,則陽蹺之病不至陰緩陽急,陰蹺之病不至陽緩陰急,何不驗乎。
司馬公曰:今而後,陰陽二蹺之脈昭然矣。
陳士鐸曰:二蹺之脈,分諸男女。《內經》微別,人宜知之,不可草草看過。
奇恒篇第二十二
奢龍問于岐伯曰:奇恒之腑,與五臟並主藏精,皆可名臟乎?
岐伯曰:然。
奢龍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既謂奇恒之腑,不宜又名臟矣。
岐伯曰:腑謂臟者,以其能藏陰也。陰者,即腎中之真水也。真水者,腎精也。精中有氣,而腦髓骨脈膽女子胞皆能藏之,故可名腑,亦可名臟也。
奢龍曰;修真之士,何必留心於此乎?
岐伯曰:人欲長生,必知斯六義,而後可以養精氣,結聖胎者也。
奢龍曰:女子有胞以結胎,男子無胞何以結之?
岐伯曰:女孕男不妊,故胞屬之女子,而男子未嘗無胞也,男子有胞而後可以養胎息,故修真之士必知。斯六者至要者則胞與腦也,腦為泥丸,即上丹田也;胞為神室,即下丹田也。骨藏髓,脈藏血,髓藏氣,腦藏精,氣血精髓盡升泥丸,下降於舌,由舌下華池,由華池下廉泉玉英,通於膽,下貫神室。世人多欲,故血耗氣散,髓竭精亡也。苟知藏而不瀉,即返還之道也。
奢龍曰:六者宜藏,何道而使之藏乎?
岐伯曰:廣成子有言,毋搖精,毋勞形,毋思慮營營,非不瀉之謂乎。
奢龍曰;命之矣。
陳士鐸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非臟也,非臟而以臟名之,以其能藏也,能藏故以臟名之,人可失諸藏乎。
小絡篇第二十三
應龍問于岐伯曰:膜原與肌腠有分乎?
岐伯曰:二者不同也。
應龍曰:請問不同?
岐伯曰:肌腠在膜原之外也。
應龍曰;肌腠有脈乎?
岐伯曰:肌腠膜原皆有脈也,其所以分者,正分於其脈耳。肌腠之脈,外連于膜原,膜原之脈,內連於肌腠。
應龍曰:二脈乃表裏也,有病何以分之?
岐伯曰:外引小絡痛者,邪在肌腠也。內引小絡痛者,邪在膜原也。
應龍曰:小絡又在何所?
岐伯曰:小絡在膜原之間也。
陳士鐸曰:小絡一篇,本無深文,備載諸此。以小絡異于膜原耳,知膜原之異,即知肌腠之異也。
肺金篇第二十四
少師問曰:肺金也,脾胃土也,土宜生金,有時不能生金者謂何了?
岐伯曰:脾胃土旺而肺金強,脾胃土衰而肺金弱,又何疑乎。然而脾胃之氣太旺,反非肺金所喜者,由於土中火氣之過盛也。土為肺金之母,火為肺金之賊,生變為克,烏乎宜乎。
少師曰:金畏火克,宜避火矣,何又親火乎?
岐伯曰:肺近火,則金氣之柔者必銷矣。然肺離火,則金氣之頑者必折矣。所貴微火以通薰肺也。故土中無火,不能生肺金之氣。而土中多火,亦不能生肺金之氣也。所以烈火為肺之所畏,微火為肺之所喜。
少師公曰:善。請問金木之生克?
岐伯曰:肺金制肝木之旺,理也。而肝中火盛,則金受火炎肺,失清肅之令矣。避火不暇,敢制肝木乎了即木氣空虛,已不畏肺金之刑,況金受火制,則肺金之氣必衰,肝木之火愈旺,勢必橫行無忌,侵伐脾胃之土,所謂欺子弱而淩母強也。肺之母家受敵,禦木賊之強橫,奚能顧金子之困窮,肺失化源,益加弱矣。肺弱欲其下生腎水難矣,水無金生則水不能制火,毋論上焦之火焚燒,而中焦之火亦隨之更熾甚,且下焦之火亦挾水沸騰矣。
少師曰:何肺金之召火也?
岐伯曰:肺金,嬌臟也,位居各臟腑之上,火性上炎,不發則已,發則諸火應之。此肺金之所以獨受厥害也。
少師曰:肺為嬌臟,曷禁諸火之威逼乎,金破不鳴斷難免矣。何以自免於禍乎?
岐伯曰:仍賴腎子之水以救之。是以肺腎相親更倍于土金之相愛。以土生金,而金難生土。肺生腎,而腎能生肺,晝夜之間,肺腎之氣實彼此往來兩相通,而兩相益也。
少師曰:金得水以解火,敬聞命矣。然金有時而不畏火者,何謂乎?
岐伯曰:此論其變也。
少師曰:請盡言之。
岐伯曰:火爍金者,烈火也。火氣自微何以爍。金非惟不畏火,且侮火矣。火難制金,則金氣日旺。肺成頑金過剛而不可犯,於是肅殺之氣必來伐木。肝受金刑力難生火,火勢轉衰,變為寒火奚。足畏乎。然而火過寒無溫氣以生土,土又何以生金。久之火寒而金亦寒矣。
少師曰:善。請問金化為水,而水不生木者,又何謂乎?
岐伯曰:水不生木,豈金反生木乎。水不生木者,金受火融之水也。真水生木而融化之,水克木矣。
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肺不燥不成頑金,肺過濕不成柔金,以肺中有火也。肺得火則金益,肺失火則金損。故金中不可無火,亦不可有火也。水火不旺,金反得其宜也。總不可使金之過旺耳。
肝木篇第二十五
少師曰:肝屬木,木非水不養,故腎為肝之母也。腎衰則木不旺矣,是肝木之虛,皆腎水之涸也。然而肝木之虛,不全責腎水之衰者何故?
岐伯曰:此肝木自鬱也。木喜疏泄,遇風寒之邪,拂抑之事,肝輒氣鬱不舒。肝鬱必下克脾胃,制土有力,則木氣自傷,勢必求濟腎水,水生木而鬱氣未解,反助克土之橫。土怒水助轉來克水。肝不受腎之益,腎且得土之損,未有不受病者也。腎既病矣,自難滋肝木之枯,肝無水養,其鬱甚。鬱甚而克土愈力。脾胃受傷氣難轉輸,必求救於心火,心火因肝木之郁全不顧心,心失化源,何能生脾胃之土乎。於是憐土予之受傷,不敢咎肝母之過,逆反嗔肺金不制肝木,乃出其火而克肺,肺無土氣之生,複有心火之克則肺金難以自存。聽肝木之逆,無能相制矣。
少師曰:木無金制宜木氣之舒矣,何以仍鬱也?
岐伯曰:木性曲直,必得金制有成。今金弱木強,則肝寡于畏,任鬱之性以自肆,土無可克水,無可養火,無可助,於是木空受焚矣。此木無金制而愈鬱也。所以治肝必解鬱為先,郁解而肝氣自平。何至克土,土無木克則脾胃之氣自易升騰,自必忘克,腎水轉生肺金矣。肺金得脾胃二土之氣,則金氣自旺,令行清肅。腎水無匱乏之憂,且金強制木,木無過旺肝氣平矣。
少師曰:肝氣不平可以直折之乎?
岐伯曰:肝氣最惡者鬱也。其次則惡不平,不平之極即鬱之極也。故平肝尤尚解鬱。
少師曰:其故何也?
岐伯曰:肝氣不平,肝中之火過旺也。肝火過旺,由肝木之塞也。外閉內焚,非爍土之氣即耗心之血矣。夫火旺宜為心之所喜,然溫火生心,烈火逼心,所以火盛之極,可暫用寒涼以瀉。肝火鬱之極,宜兼用舒泄以平肝也。
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木不鬱則不損,肝木之鬱即逆之之謂也。人能解鬱,則木得其平矣。何鬱之有。
腎水篇第二十六
少師曰;請問腎水之義。
岐伯曰:腎屬水,先天真水也。水生於金,故肺金為腎母。然而肺不能竟生腎水也,必得睥土之氣薰蒸,肺始有生化之源。
少師曰:土克水者也,何以生水?
岐伯曰:土貪生金,全忘克水矣。
少師曰;金生水而水養于金,何也?
岐伯曰:腎水非肺金不生,肺金非腎水不潤。蓋肺居上焦,諸臟腑之火,鹹來相逼,苟非腎水灌注,則肺金立化矣。所以二經子母最為關切。無時不交相生,亦無時不交相養也。是以補腎者必須益肺,補肺者必須潤腎,始既濟而成功也。
少師曰:腎得肺之生即得肺之損,又何以養各臟腑乎?
岐伯曰:腎交肺而肺益生腎,則腎有生化之源。山下出泉涓涓正不竭也。腎既優渥,乃分其水以生肝。肝木之中本自藏火,有水則木且生心,無水則火且焚木,木得水之濟,則木能自養矣。木養于水,木有和平之氣,自不克土。而脾胃得遂其升發之性,則心火何至躁動乎。自然水不畏火之炎,乃上潤而濟心矣。
少師曰:水潤心固是水火之既濟,但恐火炎而水不來濟也。
岐伯曰:水不潤心,故木無水養也。木無水養肝必乾燥,火發木焚,爍盡脾胃之液,肺金救土之不能,何暇生腎中之水。水涸而肝益加燥,腎無瀝以養肝,安得餘波以灌心乎!肝木愈橫,心火愈炎,腎水畏焚,因不上濟於心,此腎衰之故,非所謂腎旺之時也。
少師曰:腎衰不能濟心,獨心受其損乎?
岐伯曰:心無水養,則心君不安,乃遷其怒于肺金,遂移其.火以逼肺矣。肺金最畏火炎,隨移其熱於腎,而腎因水竭,水中之火正無所依,得心火之相會,翕然升木變出龍雷,由下焦而騰中焦,由中焦而騰上焦,有不可止遏之機矣。是五臟七腑均受其害,寧獨心受損乎!
少師曰:何火禍之酷乎?
岐伯曰:非火多為害,乃水少為炎也。五臟有臟火,七腑有腑火,火到之所,同氣相親,故其勢易旺,所異者,水以濟之也。而水止腎臟之獨有,且水中又有火也。水之不足,安敵火之有餘。此腎臟所以有補無瀉也。
少師曰;各臟腑皆取資于水,宜愛水而畏火矣。何以多助火以增焰乎?
岐伯曰:水少火多,一見火發,惟恐火之耗水,竟來顧水,誰知反害水乎。此禍生於愛,非惡水而愛火也。
少師曰:火多水少,瀉南方之火,非即補北方之水乎?
岐伯曰:水火又相根也。無水則火烈,無火則水寒,火烈則陰虧也,水寒則陽消也。陰陽兩平,必水火既濟矣。
少師曰:火水既濟獨不畏土之侵犯乎?
岐伯曰:土能克水,而土亦能生水也。水得土以相生,則土中出水,始足以養肝木而潤各臟腑也。第不宜過於生之,則水勢汪洋亦能沖決堤岸,水無土制,變成洪水之逆流,故水不畏土之克也。
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五行得水則潤,失水則損。況取資多而分散少乎。故水為五行之所窈,不可不多也。說得水之有益,有此可悟永矣。
心火篇第二十七
少師曰:心火,君火也。何故宜靜不宜動?
岐伯曰:君主無為,心為君火,安可有為乎!君主有力,非生民之福也。所以心靜則火息,心動則火炎。息則脾胃之土受其益,炎則脾胃之土受其災。
少師曰:何謂也?
岐伯曰:脾胃之土喜溫火之養,惡烈火之逼也。溫火養則土有生氣而成活土,烈火逼則土有死氣而成焦土矣。焦火何以生金,肺金乾燥,必求濟于腎水,而水不足以濟之也。
少師曰:腎水本濟心火者也,何以救之無裨乎?
岐伯曰:人身之腎水原非有餘。況見心火之太旺,雖濟火甚切,獨不畏火氣之爍乎。故避火之炎,不敢上升於心中也。心無水濟則心火更烈,其克肺益甚。肺畏火刑,必求援於腎子,而腎子欲救援而無水,又不忍肺母之淩爍,不得不出其腎中所有,傾國以相助。於是水火兩騰,升于上焦,而與心相戰。心因無水以克肺,今見水不濟心火來助肺,欲取其水而轉與火,相合則火勢更旺。於是肺不受腎水之益,反得腎火之虐矣。斯時肝經之木,見肺金太弱,亦出火以焚心明助腎母,以稱於實報肺仇而加刃也。
少師曰:何以解氛乎?
岐伯曰:心火動極矣,安其心而火可息也。
少師曰:可用寒涼直折其火乎?
岐伯曰:寒涼可暫用,不可久用也。暫用則火化為水,久用則水變為火也。
少師曰:斯又何故歟?
岐伯曰:心火必得腎水以濟之也。滋腎安心則心火永靜,舍腎安心則心火仍動矣。
少師曰:凡水火未有不相克也,而心腎水火何相交而相濟乎?
岐伯曰:水不同耳。腎中邪水最克心火,腎中真水最養心火,心中之液即腎內真水也。腎之真水旺,而心火安。腎之真水衰,而心火沸。是以心腎交而水火既濟,心腎開而水火未濟也。
少師曰:心在上,腎在下,地位懸殊,何彼此樂交無間乎?
岐伯曰:心腎之交,雖胞胎導之,實肝木介之也。肝木氣通,腎無阻隔,肝木氣鬱,心腎即閉塞也。
少師曰:然則肝木又何以養之?
岐伯曰:腎水為肝木之母,補腎即所以通肝木。非水不旺火,非木不生欲,心液之不枯,必肝血之常足。欲肝血之不乏,必腎水之常盈,補肝木要不外補腎水也。
少師曰:善。
陳士鐸曰:心火,君火也。君心為有形之火,可以水折。不若腎中之火,為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可以水養。知火之有形、無形,而虛火,實火可明矣。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